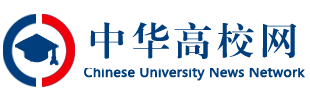他的世界黑白分明。
白粉笔在黑板身上安静走路,一笔一画不敢造次,一数字一符号天机暗藏,凸起的理路背后是沉静而生气勃勃的手指,是专注而深情脉脉的眼眸,是连通天地俯仰古今的胸襟。他平行于黑板,黑板垂直于地面,这是数学的世界,直角和顶点之外,亦有柔软,亦有留白,亦有审美的意味。
他在高二空降,接管一个号称快班、成绩垫底的班级。前任班主任家事繁冗,班级管理失控。他一到来,先是阻止足球的飞动。班长整日带着一群男生追着一只足球跑,扬起的沙尘隐没了少年的初心。有一天,足球穿破窗户,飞过我的饭盒,又从另一扇窗户飞了出去,伴着“砰”的一声巨响,我就着饭里的灰尘吃了下去。这只足球被他生生接住,班长在众目睽睽下垂头检讨。所有的躁动都被压平,他走过的地方温度骤降。期末分数像秋后的庄稼,长势喜人。
毕业会考来临。我们刚在慈祥的化学老师那里沐浴过春风,他就冲了进来,下了一场愤怒的雨,末了,报了一串“不得好死”的名字,我也是其中之一。他转身,比来时更快地冲了出去,一室死寂,没有人从自己的座位上站起来,我咬紧牙关把尿憋了回去。后来,我却被他狠狠地表扬了,数学考试我比那些所谓的聪明人、尖子生都好,我不平衡的心被他抚平了。我偷偷地看他的背影,脑袋圆,身材方,头发黑浓,一根一根直竖着,毫不妥协,爱憎分明。
他的世界不止于黑白。
我进了文科班,莫名其妙地成了他的科代表。我总是趁他不在时去拿同学们的作业本,因为害怕还常常忘记拿,害得他自己送过来,却毫无生气的意思。我报考师范,提前录取,他说真没想到,惋惜像一层厚厚的油发出苍白的光。我是从他班里出去的人,又是以班里第一名的成绩进入文科班的,我确实辜负了他的厚望。我毕业后回到母校做班主任,他把好友的孩子放在我班上,相信我带到高三会耕出丰饶。后来,受困于失眠和无法调适的心理状态,我主动离开了班主任岗位,这似乎还拖累了他。我,普通家庭的孩子,毫无出色之处,老实本分,甚至有点儿呆傻,却得到了他一视同仁的对待,领受了他慷慨无私的爱。
他的软笔书法很好,油画更是出名。退居二线的他安于画室,寄情斑斓,快意于黑白之外的大千世界。总是想起他的粉笔字,匀称,俊秀,转折和收尾特别用力,英气外溢,好像士兵庄重的致敬,又似将军铿锵的手势,甚至带出侠客掠身上马、长衣翻飞的意气,宣示着什么,含蓄着什么。书画交融的乾坤,自有一股风流。
他的世界仿佛还有杂色,斑驳迷离。
他退居二线,众说纷纭,真假难辨,唯一的真实是,他从云上落到地上,退出了数学世界。多年以来,我的耳边流言不断,而我再也没有看到他,偶尔去他所在的学校监考改卷,他仿佛消失在人群中。有一次好像看到他的影子,我却不敢走上前,恭敬地叫一声,许老师。虽然我的心里是叫了无数次的。
我承认,我的心里是有想法的。虽然我们都有一颗追求不凡的心,我们却有一对浅尝辄止的耳朵。耳朵里进了水,就会陷于糊涂的境地。耳朵是最软的,轻易缴械,毫无原则。天生的劣根性使我们堵塞昏昧,喑哑失声,犯下大错而不自知,背弃善良而不自省。没有眼睛,或许更能洞察,没有耳朵,或许更能分辨。
幸好,我做了老师,有了亲历亲证的机会。经过我人生的所有老师,和我一起创造了丰富的生命故事。无论他们是怎样的人,他们都以自己的方式给予我独特的关怀,无论他们遭遇什么,他们最终都以清水洗尘、清泉漱心的人格魅力浸润了我的身心。也许他们曾经陷于人世的污浊和人性的沼泽而难以自清,但这并不影响我对他们的驻足回首,仰望缅怀。当他们因人性的弱点或无常的天意而在世人面前呈现窘态乃至委琐时,我却觉得这才是生活的全部真义。他们丰富这个世界的存在,提醒我人类自身的残缺,修正我看待世界的角度,因此更加宽纳和理性,并在追求真善美的道路上愈加清明和坚定。
眺望世界,能够留下背影的人越来越少。因为天上的星光越来越黯淡,也因为人们心中的光芒越来越模糊。而我的心中铭记了那么多的背影,他们黑色的影子渐渐融入时空深处,最终变成一束光。所有远逝的人蛰伏在隐秘的时空深处,以黑夜才能听懂的声音召唤我们的灵魂回家。
他们的世界是水晶球,投射万物,折射光芒,斑斓不可方物,深沉有如神谕。
(作者范玲玲系浙江省绍兴市第一中学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