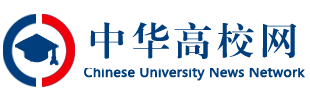我与杨叔子院士过从不密,多为神交,但有一次交集,却是终生难忘,堪称奇缘。我想借此机会形诸笔端,以存没世不忘之念。
2002年,教育部开始评选国家级精品课程,我在清华主讲的“文物精品与文化中国”居然在两轮投票中全票通过。不过,我并没有特别欣喜,因为评审专家都不听课,是根据申报材料投的票;再说,该课程并非我的专业特长。我在清华开设的“中国古代礼仪文明”课,乃是荟萃“三礼”而成,更能体现我的学术水平,2008年,我准备申报国家精品课。真是无巧不成书,那年5月,教育部对全国高校实施教学评估,以杨叔子院士为组长的专家组一行二十余人进驻清华,当天下午,在清华主楼后厅召开全校教授与干部大会,介绍工作方式与注意事项等。所有专家组成员都要下去听课,由抽签确定所听课程。我想,若能请杨先生亲自听我一堂课,即使评不上精品课我亦心甘。
不少青年教师害怕被抽中,而我则唯恐失去这次机会。为此,散会后我候在会议厅门口。杨先生出门后我上前打招呼,他停下脚步,微笑着问我:“找我有什么事?”我说:“后天晚上我正好有一门课,想请您到教室里指导,不知道有没有这个荣幸?”杨先生微微歪着脑袋、略带调皮的表情说:“我这次来清华,就是想听你的课。”听闻此言,我真是高兴无比。
我那天要讲的课的主题是:《仪礼》记载的“乡射礼”。射箭比赛的缘起,国际奥组委下属国际箭联的章程说,是由英国贵族在16世纪所发明。殊不知中国早在公元前8世纪就已盛行乡射、大射、燕射等各种名目的比赛,将比射与礼仪融合为一,称为“文射”,以此涵养君子之德,展现君子风范,人文内涵极其丰富。
上课那天,杨先生与他的助手余东升老师早早到场。余老师对我说:“今天的课,杨先生只能听前半节,因为评估组每天晚上都要碰头,汇总当天调研的信息。”清华的课以85分钟为一大节,前后各一小节,都是40分钟,中间有5分钟休息。我顿时觉得很失落,因为这堂课的前半段属于背景铺垫,后半段才是我的研究心得之所在。如果只听前半部分,则等于没听。奈何?我紧急决定,调整课程节奏,压缩前半段的内容,尽量将后程内容提前,并从容发挥,激发杨先生的兴趣,力争使他不忍离去。
教室有280个座位,我请杨先生前排就座,杨先生不同意,执意坐在最后几排靠右边的座位。为了避免学生紧张,我没有把教育部专家组组长就在我们教室听课的消息告诉大家,我希望能让杨先生看到我日常的教学。
我那天的开场白比较“抓人”:“同学们!北京奥运不到一百天就要开幕了,我想问大家:你们都准备好了吗?”
只见学生们面面相觑:“我们又不是奥组委的,我们准备什么?”
我接着说:“如果我是一名外国记者,一定会到清华大学来采访,因为清华是中国的最高学府之一。我会提出如下三个问题:一、中国是文明古国,那么中国古代有体育吗?二、如果有体育,那么有体育精神吗?三、如果有体育精神,请问,它与古希腊奥运会的体育精神相比,孰优孰劣?”
学生听完全傻了,没人考虑过这些问题。于是,我缓缓地说:“今天这堂课,我试图来回答这三个问题。”这时,全场学生的注意力全被我调动起来,都想听我的答案。我朝教室后方望去,杨先生端端正正地坐着,眼镜的镜片泛着亮光,我想,他一定也想听我的答案。
我从卜辞、金文记载的射箭讲起,讲到周代礼乐文明,再导入乡射礼的过程与内涵,步步深入。第一小节的下课铃声响了,作为评估组的秘书,余东升老师起身离场,而杨先生安坐不动,这给了我极大的信心。为了保证课堂气场的连贯,我课间没有休息,一口气讲到下课铃响,自我感觉不错,学生掌声热烈至极,杨先生也鼓掌。至此,我才告诉学生们:“教育部评估组组长杨叔子院士今天亲临听课!”学生大为惊喜。我请杨先生对当天的教学过程批评指导。杨先生站起来朝学生们拱了拱手,没有说话,随即离场。次日上午,清华校办的一位老师给我来电话,说当晚杨先生听完课回到专家组讨论的会议室,对我赞不绝口,说:“这个彭林,居然把一个古代体育专题讲得这么精彩!”专家组结束在清华的评估后,转场东南大学,不料,东南大学又有校部机关的朋友告诉我:“杨先生到我们这里提到你的课,评价很高啊!”这令我非常感动,这是我一生中唯一一堂有中科院院士的专家在场、端坐听完全程的课,弥足珍贵、毕生难忘。此年秋,我的“中国古代礼仪文明”经杨先生主持的评委会投票,入选国家精品课,我未私托,杨先生亦无私诺,干干净净,令人欣慰。
此后,杨先生几次邀请我到华工的大讲堂作讲演,每次,他都会亲自到酒店看望,问长问短,令人倍觉温暖。其中一次,适逢教育部高等学校文化素质教育指导委员会在华工开会,杨先生特意安排我晚上到校内的爱因斯坦广场作讲演,说是学生在宿舍开着窗就可以听到,影响会更大。承杨先生厚爱,这成为我此生唯一作过的一场露天讲演。
杨先生一生培养的博士逾百位,他要求每位学生都要背《老子》、读《论语》,在文化上传承中华文明的衣钵。我看网络报道,在杨先生的遗体告别仪式上,弟子送的花圈,在离杨先生灵柩最近处摆成一长列,下款一律写着“学生某某”,犹如一排树木,肃然而壮观。我不由得想起《山海经》里“与日逐走”的夸父,这是一位敢于与太阳赛跑的史诗级的英雄,夸父渴极,饮干了河、渭,又北饮大泽,最后还是道渴而死。夸父“弃其杖,化为邓林”,他留下的手杖,化为郁郁葱葱的树林。杨先生的一生堪与夸父相比,他遗下的手杖,不亦化作了这一片“邓林”?
(作者彭林系清华大学文科资深教授、浙江大学马一浮书院兼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