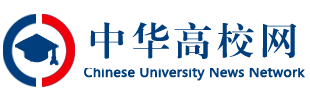潘懋元先生走了!噩耗传来,万分悲痛。教师节前夕,我给厦大教育研究院别敦荣教授打电话,问候潘先生。别教授告诉我,潘老4月中旬因肺炎住院,神志清楚,正在恢复中。我想,潘老身体底子较好,一直注意锻炼,90多岁还每天做俯卧撑,一定能恢复过来。没想到,这次竟然没有能挺过来,使我无限悲伤。
潘老长我9岁。1952年,他在北师大教师进修班研修。如果当时我不是在苏联学习,他就是我的老师了。直到1979年第一次教育科学规划会议期间我们才认识,至今40多年了,我们的交往最多、最频繁、最亲密。如果以10年为人生的一代人,潘老是我的先辈,我们的友谊可谓忘年之交了。
1978年,厦门大学成立高等教育研究室,不久成立研究所。1979年,北师大在外国教育研究室的基础上成立外国教育研究所。20世纪80年代初,我们都开始招收硕士研究生。当时,大家对学位研究生培养都没有经验。在潘老的倡议下,20世纪80年代初,曾经在北师大召开过有厦大、北大、北师大参加的如何培养高等教育硕士研究生问题的研讨会。潘老在那次会议上提出了许多宝贵意见。
1983年9月,我们共同参加了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学科评议组会议,以后又共同担任了第二、三届教育学科评议组的召集人。从此,我们几乎每年都会见面,研究讨论教育学科的研究生专业目录和研究生培养工作,评议硕士、博士授权点和博士研究生导师的资格等事宜。在教育学科评议组工作时间,我们同住一个房间,共同主持会议,合作得非常愉快。
1986年秋,国家教委高教司在泉州华侨大学召开高等教育研讨会,潘老和我都参加了。会后,潘老邀请我到厦大讲学,这是我第一次访问厦门大学。潘老热情地招待我,陪我参观了厦大花园般的校园、周边的名胜古迹。因为我是北师大校友会副会长,潘老是北师大厦门校友会会长,还特地安排了一次北师大校友与我见面,热情的场面至今难忘。
20世纪90年代初,国家酝酿制定高等教育法,成立专家组,我和潘老都参加了。1994年1月,在成都四川大学召开了高等教育法第一次专家咨询会。此后,讨论、起草、修改,开了无数次会议。我记得,修改稿共有18稿之多。经过多年磨炼,《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终于在1998年8月29日由第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四次会议通过。制定高等教育法,我和潘老参与了全过程。在讨论过程中潘老提出了许多有益的意见。
2000年,厦门大学以高教所为依托获批成立高等教育发展研究中心,成为全国普通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潘老任中心主任。中心成立学术委员会,潘老聘任我为学术委员会主任委员。此后几年,每年毕业季,潘老都邀请我到厦门大学主持博士论文答辩会,与研究生座谈、讲演。中心举办的多次国际教育论坛和研讨会,我几乎都参加了。所以,每年我们都能见面,交流教育工作中的问题。最近一次见面是2017年11月,我参加厦大高教研究中心举办的高等教育论坛。潘老以97岁的高龄参加了两天的会议,倾听各位代表的发言。我着实佩服他的精神。可惜的是,2020年潘老百岁华诞庆典,我因疫情未能参加,成为永久的遗憾。
以上是我和潘老的几次重大合作,至于其他交往就更多了。我们都受聘于原教育部教育发展研究中心专家咨询委员,每年开会都在一起讨论教育发展的战略问题和热点问题。我们还共同参加了许多教育学术会议。1991年6月,我们一起作为中国高等教育代表团成员访问了苏联。那时正是苏联解体前夕,我们亲眼看到苏联的衰败景象,心里十分难过。
同潘老的密切交往中,我学习到许多东西。在学术上,潘老是我国高等教育学的创始人、奠基人。潘老总是站在时代的前沿,高瞻远瞩,放眼世界,在耄耋之年仍出访欧美各地,奔走于中国大江南北,调查研究,发表演讲,推动着教育改革,为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在教学上,潘老严谨治学,诲人不倦。他一直亲自授课,从没有离开过讲台,培养了一大批高等教育研究人才。前年,我的一名学生到厦大教育学院访学,参加了潘老每周六晚上在家里举行的学术沙龙,几十名学生济济一堂,热烈讨论,直到晚上10点钟才结束,感到十分震惊,十分钦佩,真是一位大先生,教书育人的楷模。
在为人上,潘老真诚朴实,平易近人,一点儿没有学术权威的架子。他喜欢和年轻人在一起,听取他们的意见。他乐于助人,我们在合作交往中,他给予我很大的帮助和支持。我在编纂《教育大辞典》时,请他担任顾问,他欣然答应,并且认真地参加编委会会议,给予了很多指导。
我们的友谊真的说不完。现在他走了,但他的精神永存,我永远怀念他!
(作者顾明远系北京师范大学资深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