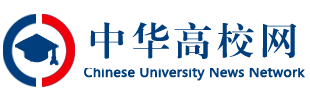寰宇无穷,盈虚有数,前不见古人,后更有来者。作为宇宙间的智识生命,人类自古就走在孤独求索的道路上。现代的科学世界图景的渊源可远溯至古希腊,彼时还无所谓“科学”,而纷呈的“科学观”恰恰蕴藉于哲学之思。
在《科学的七大支柱》([英]约翰·格里宾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中,约翰·格里宾首先将我们带回到古希腊。来自地外的一颗陨石的火光,映在阿那克萨戈拉的眼眸里,也给他带去了内心的光亮。这位哲人秉持科学态度对太阳神圣性的否定,使他遭受了不公的驱逐,但也启迪了两百多年后的埃拉托色尼,为后者更准确地计算地球的半径打下了基础。文艺复兴前后,自然之光使人的肉眼更不满足于庸常的判断,进而人们将目光投向天际,甚至无畏于宗教强权——一如火刑架上的布鲁诺,呼出振聋发聩的声音。
从天文学到微观物理学,世界的宏大和微小,在人类思想之际只是须臾。在理查德·费曼口中的“原子假说”和德谟克利特的“原子论”之间,是人类两千多年来在难言之物上的思想接力,也是实与虚的问题由虚到实的过程。厌恶原子虚空观念的牛顿,以其对自然哲学之数学原理的探究,为自然规划了一幅和谐的图景。但直到20世纪初,原子理论才得以确立。显微镜下的布朗运动带来的是人类对无生命之物运动的惊奇,爱因斯坦回归源头的思考和基于阿伏伽德罗常数的证明,才将观察语言真正转变为理论语言,并为热分子动力学正名。
探微知著,格里宾通过展示宇宙间构成生命的元素比例,使我们明白了科学研究的终极意义指向——人作为有智识的生物,其生有涯而知无涯,所以求知探索终究要回到大地,朝向生命和自身。格物穷理,理却无穷。虽说“生命力”的观念自古就有,却长久处于人类知识的晦暗地带。直至19世纪20年代,弗里德里希·沃勒完成尿素的人工合成,才撼动了人们对生命力观念的执着。马塞林·贝塞洛和比希纳在有机化学领域的卓绝工作最终使活力论成为历史,将科学理性带至对生命何以可能的追问。
20世纪的生命科学研究激动人心,对生命密码的破译甚至跨越了学科的界限。薛定谔说:“人们通常认为,科学家对某些学科拥有全面而深入的一手知识,因此他不会就他并不精通的论题去著书立说。这就是所谓的位高则任重。”但作为量子力学重要奠基者之一,他还是掷地有声地问出了“生命是什么?”并以此推动了科学界对生命密码的执着探求。伴随着生物化学和医学的研究进展,被称为DNA的“非周期性晶体”的细节得到了破译。进而,DNA分子的双链结构何以可能,成为生命因果链溯源中的关键问题。至此,格里宾才带出了本书的核心线索“冰难以置信的轻”,从关于水与冰的日常经验,讲到生命演化的奥秘。
鉴于此书的科普性质,格里宾没有进一步展开量子力学层面对氢原子的研究,但他对氢键优势的讲述简单而明晰。氢原子以其独有特性可以与带有多余负电荷的原子形成较弱的连接,这解释了DNA何以能够形成其重要的形状。此外,氢键的性质使水得以在海洋里低于冰点的环境中存在,于是地球在经历了数次“雪球”事件后依旧可以留存大量的水。这为生命的演化创造了最基本也最重要的条件,也是格里宾将氢键定为最重要的科学支柱的原因。
科学的支柱促成现代科学世界图景的建构,而自然之光和理性之光是这些支柱得以矗立的根源。对于读者而言,一本好的科普著作会为世界观的拼图补上关键的缺块,同时也为接合既有部分提供路径的指引。作为读者,我认为只有对世界怀有常新的惊奇,点亮内心之光,才能使自己眼中的科学世界图景日臻完整。(钟远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