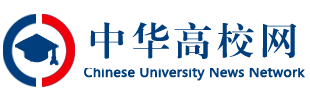提起笛卡尔,大家耳熟能详的就是他那句名言“我思,故我在”。甚至在教科书中,也因为这句话,把笛卡尔定性为“主观唯心主义者”。
这种定义当然也有一定的道理,但也是不全面的。其中应该参考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意见就来自马克思和恩格斯。他们不是只从单方面去看待人,特别是像笛卡尔这样的哲学家。在《神圣家族,或对批判的批判所做的批判》中,他们曾这样评价笛卡尔的哲学:
“法国唯物主义有两个派别:一派起源于笛卡尔,一派起源于洛克。后一派主要是法国有教养的分子,它直接导向社会主义,前一派是机械唯物主义,它汇入了真正的法国自然科学。”(引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一卷)
显然,马恩不仅将笛卡尔视为唯物主义者,甚至将他定为“法国自然科学”的源起。其中缘由,需从笛卡尔哲学的整体去理解。
关于各学科的关系,笛卡尔有这样一个我们耳熟能详的比喻:“整个哲学如同一棵树:树根是形而上学,树干是物理学,从树干上长出的树枝就是所有其他的科学。”在这里,笛卡尔将一切学科视为一个体系,它们就像数字一样彼此联系。如此,树干才能滋润枝叶和果实。
然而,人们通常把这种比喻理解为:形而上学是这些学科体系中最为重要的根基。这种解释当然不无道理,但也会引起误导,因为笛卡尔曾明确将自己的哲学目标视为为人类利益所服务。这意味着,“树根”虽然滋养枝叶,但结果的不是树根而是枝干,所以这应是一种“实用的哲学”。“人不是从树根或树干上采摘果实,而只能从树枝上采摘”,因为它们对生活最有用,并最终使我们成为“自然的主人”(引自《谈谈方法》第六部分)。因而,作为树根的形而上学只是获得果实的手段,并不是目的。对笛卡尔来说,那些形而上学的问题与抽象概括的方法一样,并不是他学术之旨趣,而是具有实用目的的。他也常常告诫朋友和书信伙伴,不要沉溺于形而上学的追问。1648年,在与布尔曼(Burman)的一次会话中笛卡尔这样说道:
“不应该把太多精力用于《沉思集》和形而上学的那些问题上,在进行评论等事情时做得很仔细。……否则,你的心灵就会偏离物理世界和可见事物太远,不能适应它们了。而正是这些物理方面的研究,才是我们最渴望追求的,因为它们将为生活提供大量的益处。”
据说,将笛卡尔视为“唯理论”的形而上学家,以第一原理来演绎物理真理的说法,最早来源于19世纪。库诺·菲舍(KunoFisher)在他的《近代哲学史》中,首次做了详细的描述。他是一位康德主义者,旨在向读者表明:康德哲学可以解决现代思想中的主要难题。为此,他把近代以来的前康德哲学分为我们今天熟悉的两派:唯理论与经验论,前者把一切都建立在理性真理的基础之上,后者则建立于经验之上。这种划分以认识论为主导,使17世纪成为近代哲学的一个标志性开端。
这种说法得到后来很多哲学家们的接受与认可,并且在笛卡尔那里也是可以得到印证的。在笛卡尔看来,人类知识领域的所有东西都以同样方式相互联系,因而只需要找到一种科学的方法,就可以运用于诸领域学科的研究。他的形而上学和方法论,就是为了一劳永逸地解决这些学科的基础问题,从而确立整个(广义的)哲学体系的有效性。在《哲学原理》中,笛卡尔这样提出:
“除了那些在数学里被接受的原理之外,在物理学里,我并不接受或希求任何其他原理;因为所有自然现象都是以这种方法来解释的,而且可以给出关于它们的必然性论证。”
笛卡尔的同时代学者并不会把《谈谈方法》《第一哲学沉思集》《哲学原理》等作品看成是先验论和演绎哲学,而毋宁说是看成一种假言推理模式——牛顿就曾批评他提供的这些所谓的确定性乃是假设。而从笛卡尔大量的书信中也可看到,九成部分都在讨论科学研究和实验、物理等经验世界的内容,并非哲学家关注的形而上学问题。我们也可以发现,其中也充斥着很多科学实验的工作。这些才应该是笛卡尔“谈方法”这类形而上学问题的实用意图。例如《谈谈方法》还有一个附录名,即“屈光学、天象学和几何学——它们皆为本方法的尝试”。
作为近代哲学之父,笛卡尔不仅给我们带来了奠基性的形而上学,更为近代科学提供了精确和细致的研究方法。无论是哲学爱好者还是年轻的学生读者,了解一个更准确、更全面的笛卡尔,都是一件很有必要的事。值得一提的是,新近出版的这本《笛卡尔指南》,就为我们了解这位解析几何创造者的生平与思想,以及破除他身上的符号化标签,提供了不错的读本。唯有真正了解笛卡尔的思想,我们才会知道,原来认为“我思”与“怀疑”最为重要的笛卡尔,更是一位唯物主义哲学家。
(作者郝春鹏系上海师范大学哲学系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