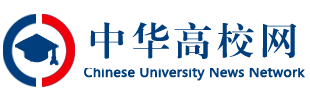随看随想
乔姆斯基是著名的语言学家、哲学家。本文是他结合最新的心智研究,对该主题前景的一个探讨。他针对语言研究的四个问题展开,更多的是提出问题。语言如何习得,由哪些物理机制决定和影响?为什么语言这样简单的技能需要大量的经验和训练?作者通过这些问题引发我们思考,在行文中也有对语言教学的一些真知灼见,比如要关注学生的好奇心等。(杨赢)
——————————————
我的讲座从语言研究中出现的四个中心问题开始:
(1)当我们能够说并理解一种语言时,我们都知道些什么?
(2)这种知识是如何获得的?
(3)我们是如何运用这种知识的?
(4)涉及这种知识的表征、获得和使用的物理机制有哪些?
第一个问题在逻辑上先于其他问题。我们对问题(1)的答案有一定了解之后,才能继续探讨问题(2)(3)和(4)。
对问题(1)的回答基本上是描述性的。在完成该任务的过程中,我们试图构建一种语法,即用来描述某一特定语言如何为每个语言表达式指派具体的心理表征,确定其形式和意义的一种理论。第二项任务更为艰巨,需要我们做出真正的解释。为了完成该任务,我们试图创建一种普遍语法理论,一种有关构成人类语言机能固定不变的原则和与之相关的变异参数的理论。通过以某种方式设定参数,我们实际上能推导出特定语言。此外,有了满足普遍语法原则的词库和以特定方式设定的参数,我们就能从普遍语法的原则中派生出这些语言中句子的结构表征,从而解释它们为何具有现在的形式和意义。
问题(2)是语言研究中出现的柏拉图问题的一种特殊情况。直到我们成功地创建普遍语法的理论,才能解决这个问题,尽管也会涉及其他因素,例如设定参数的机制。在其他领域中也存在柏拉图问题的其他特殊情况,也必须以同样的方式来解决。
那么,语言学习就是确定普遍语法未能明确的参数值的过程,用我先前提到的意象来说,就是设定网络运转开关的过程。此外,语言学习者必须发现该语言的词项及其属性。这在很大程度上似乎是一个为既存概念寻找标签的问题,这种结论令人惊讶并且貌似不可理喻,然而本质上看来却是对的。
语言学习并非真正是儿童才做的事情;它是发生在处于某种恰当环境中的孩子身上的事情,就像在提供适当的营养和环境刺激下,孩子的身体会以预先规定的方式生长和成熟一样。这并非说与环境的本质毫不相干。环境决定了普遍语法参数的设置方式,从而产生出不同语言。早期的视觉环境以某种相似的方式决定了对水平线和垂直线的受体密度,实验已经证明了这一点。此外,和身体成长一样,在语言习得中,富有刺激的环境与缺乏刺激的环境之间可能存在着巨大的差别,或者更准确地说,和身体成长的其他方面一样,语言习得只是其中的一个方面。属于人类共同禀赋的能力有可能繁荣地发展,也有可能受到限制和抑制,这取决于它们成长的条件。
这种观点也许更加普遍。不应把教学比作往瓶子里灌水,而是帮助花朵以自己的方式成长,这是一种理应受到重视却没有得到足够关注的传统见解。任何优秀的教师都明白,教学方法和教材内容,远不及成功地引起学生天生的好奇心、激发他们自我探索的兴趣这般重要。学生被动学到的东西很快会被忘记。学生天生的好奇心和创造力被激发以后,他们自己发现的东西不仅会被记住,而且会为今后的探索、调查或是重要的智慧贡献打下基础。在一个真正民主的社会里,民众享有有意义、有建设性地参与制定社会政策的机会,包括他们当前的社区、工作场所和整个社会。一个把大范围的关键性决策排除在民众管理之外的社会,或者一个仅仅给予民众机会让其批准由那些掌控私人社会和国家的精英群体所做的决策的统治制度,很难配得上“民主”一词。
问题(3)包括两个方面:感知和产出。那么,我们想知道,已习得一门语言的人在理解他听到的内容和表达思想时如何运用自己的知识。在这些讲座中我已经谈到了这个问题的感知方面。但到目前为止,我并未提到产出这个方面,即我所称的笛卡尔问题,这是从语言使用的创造性方面所提出的问题,后者是一种寻常却引人注目的现象。对于一个想理解语言表达式的人而言,必须由心智/大脑决定其语音形式和词语,然后运用普遍语法的原则和参数值投射出该表达式的结构表征,确定其各个部分如何关联。我已经举过几个例子来说明该过程是如何发生的。然而,笛卡尔问题带来了一些我们未曾讨论的其他问题。
至于问题(4),我还没有讲。探讨该问题主要是将来的任务。进行这种探讨的部分问题在于,出于伦理原因,我们不会考虑把人当作实验对象。我们无法容忍以动物实验的合理方式(无论是对还是错)对人进行实验研究。因此,我们不会将儿童置于受控环境中,观察他们在不同实验设计的条件下学习了哪种语言。我们也不允许研究人员在人脑中置入电极来调查大脑内部运行情况,或通过手术切除部分大脑来确定会产生何种影响,但对除了人之外的实验对象通常会这么做。研究人员仅限于进行“自然实验”,如损伤、疾病等。试图在这样的条件下发现人脑机制是异常困难的。
就心智/大脑的其他系统而言,例如人的视觉系统,对其他生物体(猫、猴子等)的实验研究为我们提供了诸多信息,因为这些物种的视觉系统显然十分相似。但就我们所知,语言机能是人类独有的。想通过对其他动物大脑机制的研究得知人的心智/大脑机能,几乎没有可能。
与上一代人毫无异议地所接受的那些答案相比,我们今天就这四个问题给出的答案(或者在我看来,至少是我们今天应当会给出的答案)是截然不同的。就提出的这些问题而言,我们也许会给出下列答案:语言是一种习惯系统,是一种通过训练和条件限制获得的行为习惯系统。该行为的任何创新方面都是“类推”的结果。其中的物理机制本质上与接球和其他技巧行为涉及的一样。柏拉图问题未曾受到认可,被当作细枝末节而不予考虑。人们一般认为,语言“被过度地学习”;问题在于要解释这样一个事实:为何需要大量经验和训练才能获得这些简单技能。至于笛卡尔问题,也未曾在学术圈、应用学科和整个知识界中受到认可。
(选自乔姆斯基《乔姆斯基精粹》,李梅译,世纪文景出版社2021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