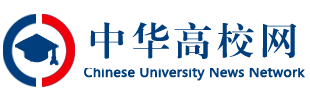多年来,每写就一文,我经常是先交给老同事徐先挺老师看看,他提出批评意见后我再进行修改。我如此看重他的意见,不仅是他有学问、有水平,更重要的是他对我很真诚,能够直言不讳地指出我写作中存在的问题,甚至彻底否定。
近年来,随着我职务的变化,听到的表扬声很多,批评意见很少。荀子说“非我而当者,吾师也”,从徐老师能指出我不足这一点,我要以他为师。
徐先挺老师20世纪90年代中期从乡镇学校调至无为中学,我们成了语文教研组的同事。他是一位诗人,年轻时曾在《诗歌报》《星星诗刊》等发表过许多作品,兴致一来,他会给我们朗诵自己的诗作。他考上大学了,漂亮的女朋友也追到了,于是骄傲地宣布:“在我的胸前,佩戴着两枚耀眼的勋章,这是考场和情场的馈赠。”他快要做父亲时,又幸福地“等待一个人,等待一位神秘的来客,等待一阵陌生的敲门声”,他的诗文采飞扬、情致动人,经常令我们拍案叫绝。
就是这样一位才子,在无为中学却出师不利,他对新的教学环境和教育对象还没有准备好,学生问他题目时,他经常答不出来。更严重的是,他不屑于做题,坚信语文教学的最终目的是教会学生读书和写作,这当然正确,但高考不仅要考作文,还要考语文基础知识、阅读理解等。学生不会做题就拿不到分数,拿不到分数就上不了大学。因此,学生和家长对徐老师意见很大,学校决定不让他上课了,由我来上他的课。徐老师一气之下,收拾行李,准备回到乡下。
听到消息后,我赶紧跑到校领导那儿帮他求情。我说,论专业功底,我和徐老师相差甚远,徐老师的教学有利于学生的长远发展,学校应该允许这样的另类教师存在,给他们更多的发展空间。我言辞恳切,校领导采纳了我的意见,徐老师也留下了,自负的他愤愤不平。不过牢骚后,他也敢于面对现实,不断调整自己,加上他良好的悟性,那一年高考成绩让人喜出望外,学校领导对他赞赏有加,我们都为他高兴。
徐老师很有教育情怀,爱生如子,但班主任生涯却早早终止。他对学校的许多规定持抵触情绪,执着于自己的教育理念,一心要释放学生的天性,认为花季年华不谈一场恋爱是人生的遗憾,最后班上的授课教师都开始对他不满,纷纷指责他。
从正统的育人理念来看,徐老师确实有点出格,但他的才华和追求非常难得。他手不释卷,光读书笔记就写了几十万字;业余时间,他笔耕不辍,在专业报刊上发表颇有影响的教学论文、随笔几十篇;他爱好书法,十多年来,每天清晨五点即起床临帖,对书法教学颇有心得。这一切为学生和青年教师树立了很好的榜样。
我在担任校长期间,每逢大型活动都要交给他一个诗朗诵的创作任务,徐老师根据校园里真实的人和事写出的诗歌感人肺腑,在师生中久久传诵。无为中学90周年校庆,他创作的《告诉未来》结尾几句是:“我,无为中学的一名学生,此刻,我站在校园的中心,东经117.4度,北纬31.2度,这是无中在全中国、全世界的位置,我抖落的文字、符号、公式精灵般化为一串串音符,未来,你听到了吗?一支昂扬的青春之歌正在唱响。”诗歌读起来荡气回肠,会场一片沸腾,全校师生的骄傲、热情、向往如阵阵热浪卷过来、涌过去。
文人清高居多,愤世嫉俗的也不少,但徐老师对人充满善意,特别能体谅领导的难处,学校工作有不到位的地方,他总是希望大家能换位思考,我们都很尊重他。但有一次我们发生了激烈的冲突。有一段时间,他不停地跟我说他到了更年期,要少上课。问他到底什么病,他又戏谑地说,此病与钱钟书《谈中国诗》一文高度吻合,含蓄、富于暗示性,大家听了只当成笑话。于是,我对他的要求置之不理。有一天我在办公室接待两位县直单位负责人,他又来说要减课的事,我仍然不答应,结果他大发雷霆,我也猛拍桌子。两位客人看得目瞪口呆。第二天,没等我找他理论,他先找上门来,请我原谅,同时正儿八经地劝告我:“当校长就是要受气的,千万别和老师计较。”
明代文人张岱说,“人无癖不可与交,以其无深情也;人无疵不可与交,以其无真气也”。徐老师的童心和真性情,还有他的“癖”与“疵”,使我们成了多年的朋友。
离开无为中学后,有一次我在路上遇见他,他谈起自己的精神状态,自诩像高三学生一样用功,说他现在的勤奋离不开我多年来给他的鼓励。他还兴高采烈地告诉我:“新校长在大会上表扬了我两次,让大家像我一样多读书、多写作。”谈笑间,他快乐得像一个孩子。
一个理想主义的老师能走多远?答案是很远很远,但还需要一些条件。一个校长能包容这样的老师,学校就多了一些生机和活力。一个人能赏识这样的同事,生活也添了许多色彩和情趣。
(作者刘 萍系安徽省无为县政协副主席、无为一中原校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