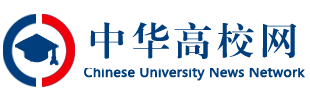2004年,法国阿维尼翁戏剧节开设了一个名为“观念的剧场”的项目,根据官网的介绍,这个项目“希望戏剧空间再次成为质疑和批评世界及其表象的地方”。安东尼·维泰兹(AntoineVitez)在《观念的剧场》一书中写道:“这始终是我想在舞台上给予的:展示思想的暴力力量。”《戏剧颂》(阿兰·巴迪欧/著蓝江/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的主体,就来自第67届阿维尼翁戏剧节的“观念的剧场”环节,它是法国哲学家、戏剧实践者阿兰·巴迪欧与尼古拉斯·张的一场公开对话。
可以说,《戏剧颂》的本质是一部戏剧档案。本书的主体部分是“对话录”,它以文字的形式记录下了对话的内容,而这场对话的发生也如一场“表演”,它遵循着线性的时间,不加停顿,稍纵即逝,充满着偶然的灵光,毫无重复的可能。在这场“表演”中,“演员”是哲学家与主持人,或者说,是两种主体性思维。因此,这场关于戏剧的对话也被戏剧这一形式所内化,正如巴迪欧在本书第二章“戏剧与哲学”中所提到的那样:“没有任何一个讨论戏剧或反对戏剧的东西能真正逃离戏剧本身。”
在巴迪欧看来,戏剧是最完整的艺术,是“发明出来的吸纳矛盾的最伟大的机制”。
戏剧起源于古希腊的酒神祭祀。在酒神节中,古希腊人对酒神狄俄尼索斯的颂歌则被称为“酒神颂”,因此,将这部对话录命名为“颂”,既有出于现代语义的考量——对戏剧的赞颂,也有对戏剧神圣起源的致敬。这场对谈的对话性,也重返了古希腊戏剧中的一个重要概念:“agon”——辩论,它原是古希腊喜剧诗人就社会与政治议题所展开的观念交锋。可以说,从“戏剧颂”这一名称出发,这部对话录的形式与内容之间产生了一种微妙的互文:对话录与对话性,当代观念与哲学传统,以及都带有明确的政治目的。而从这一互文出发,《戏剧颂》的六个章节彼此缀连,从而形成了一个有机的整体,这一整体以巴迪欧的哲学思想为底色,辩证法哲学、主体理论以及事件哲学的概念贯穿其中。
“观念的剧场”这一项目设立的初衷,意在重新建立剧场讨论现实世界的职能。戏剧在古希腊以公民义务的形态出现,它天然地被吸纳在政治的范畴中,天然地使得每一位戏剧观众成为民主政治的参与者,戏剧的政治性及其反映、批判世界的功能是与生俱来的。文艺复兴之后,以布瓦洛的《诗艺》为代表的“古典主义”戏剧弱化了戏剧的政治批判,启蒙主义时期开始蔚然成风的市民戏剧又将戏剧往另一个方向推进,最终,戏剧逐渐成为僵化了的政治工具以及市民的娱乐。19世纪末20年代初,伴随着欧洲各国集体的革命浪潮,戏剧作为一种古老的观念承载场所,开始重新找回其表现、质疑、批判社会的价值,现代性在戏剧中找到了栖身的位置。而自上世纪50年代开始,也即所谓后现代主义滥觞的时刻开始,人类逐渐被图像所包围,工业信息化社会将一切事物碎片化,堆叠出一个充满幻象的景观社会,消费主义大行其道,戏剧再次走下神坛,开始拥抱娱乐,拥抱工业化生产。这也是为什么巴迪欧认为我们与戏剧的关系是“绝对政治”的,因为此时此刻,人类身处在一个丧失严肃讨论、追名逐利的时代里,所谓观念“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急需一件武器来引导人类重新认识自己的存在,在深度的虚无主义中寻回真理。
在此,我们意识到巴迪欧的戏剧观实际是寓于他的政治哲学之中的。巴迪欧是一位典型的左派知识分子,他十分清晰地认识到剧场作为公共场所的性质,也十分坚定地要求戏剧能够如革命一般承担起时代的责任。在这里,巴迪欧的事件和主体哲学贯穿其中,他认为,戏剧中每一次表演无疑都是事件性的,将现实生活中潜藏的可能性、不确定性和偶然性带到观众面前。事件的发生意味着真实的例外的到来,它强有力地冲击了既定秩序,激发出人的强烈主体性。戏剧不论以什么方式出现(模仿或是叙述,或是更多元的后戏剧手法),它当今的使命,都是在对混乱世界的再现之中,“照亮我们生存方式和历史处境”,让观众意识到自己正身处一个真实的混乱世界,使他们获得掌控生命甚至把握社会与世界的主体性,看到生活中各种立场以及更多的可能性。
巴迪欧斩钉截铁地将自己定义为一个冷静的、不带一丝偏见的观众,他要求观众能够脱离戏剧表面所展示的幻觉,从沉浸式的享受中跳脱出来,与人物角色进行无意识的沟通,让思想在舞台与观众席之间流通。
戏剧是一种包容万千的艺术形式,它本身处在一种真实与幻觉的悖论之间,又包容了我们所发现和体验到的悖论与矛盾,一方面,戏剧在舞台上再现了现实生活的真实,另一方面,戏剧亦承载了更深层次的观念。在第三章《在舞蹈与电影之间》中,巴迪欧详细阐述了戏剧的特殊性,它处在舞蹈和电影之间,展现了“观念的内在性与超越性之间的张力”。在他看来,舞蹈是身体的内在性,舞蹈直接强调了人类身体的存在,并且向观众展示身体的无限可能性;而电影则充斥着图像,图像可以完全脱离人类而自发存在,不必求助于人本身便可以永久留存,观念由此被图像固定下来,超越了人类的生存。而戏剧将观念作用于演员的身体,身体成为一种媒介,它使观念在一场事件性的表演中得到再现,再作用于更广泛的观众。
巴迪欧的戏剧观体现了一个哲学家在当今世界中明晰的责任感。他清楚地捕捉到了时代的异化病症,并且求助于一个最强大的艺术形式来试图唤起人们的理性。尤其要指出的是,虽然在众人看来,巴迪欧是一位极为激进的左派,但罕见的,在戏剧方面,他保持了一定程度的谨慎。他敏感地捕捉到了当今蔚为大观的后戏剧作品正以一种侵略性的姿态,拆除着政治与戏剧、生活与戏剧之间的界限,行为艺术、装置艺术和表演艺术之间的边界被渐渐打破,而这种趋势将会一往无前地威胁到戏剧的再现形式,从而威胁到戏剧的存在。同时,他也一再强调戏剧与政治之间的分明泾渭,认为戏剧虽然拥有“政治的维度”,但绝不能“简化为政治架构”,也就是成为僵死的政治宣言。巴迪欧仍然坚持戏剧需要拥有特定的风格,需要文本,需要人物形象的建构。我们当然可以认为巴迪欧的姿态保守,但我们也可以认为,他想保卫戏剧“这一濒临灭绝的艺术”,一方面是为了从当前景观世界中抢救回戏剧作为公共讨论阵地的地位,另一方面,也要为不可预见的未来留存戏剧那伟大的力量。
(作者姚佳南系上海戏剧学院戏剧文学硕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