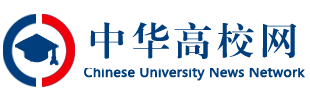随看随想
休谟的《人性论》涉及人性方方面面复杂的情况,选文谈论的是想象对情感的影响。休谟告诉我们,一般的观念会影响想象,让想象模糊,从而使情感不会生起波澜,进而影响判断。生动具体的想象则会引起生动的情感。在教育中,大道理为什么常常没有效果,恐怕也是因为这个吧。(杨赢)
想象和感情有一种密切的结合,任何影响想象的东西,对感情总不能是完全无关的:这一点是可以注意的。每当我们的祸福观念获得一种新的活泼性时,情感就变得更加猛烈,并且随着想象的各种变化而变化。这种情形是否由于上述“任何伴随的情绪都容易转入于主导的情感”的那个原则而来,我将不加断定。我们有许多例子可以证实想象对情感的这种影响,这对于我现在的目的来说,就已经够了。
我们所熟悉的任何快乐,比起我们虽认为是高一级的、但完全不知其本性的其他任何快乐来,更能影响我们。对于前者,我们能够形成一个具体而确定的观念;对于后者,我们只是在一般的快乐概念下加以想象;我们的任何观念越是一般的和普遍的,它对想象的影响便一定就越小。一个一般观念,虽然只是在某种观点下被考虑的一个特殊观念,可是通常是较为模糊的;这是因为我们用以表象一个一般观念的特殊观念,永不是固定的或确定的,而是容易被其他同样地能够加以表象的特殊观念所代替的。
希腊史中有一段著名的史实,可以说明我们现在的目的。泰米托克里斯向雅典人说,他拟就一个计划,那个计划对公众非常有利,但是他如果把这个计划告诉他们,那就必然要破坏那个计划的执行,因为那个计划的成功完全依靠于它的秘密执行。雅典人不授予他以便宜行事的全权,而却命令他把他的计划告诉阿雷司提狄斯,他们完全信赖阿雷司提狄斯的机智,并且决心盲目地遵从他的意见。泰米托克里斯的计划是秘密地纵火烧毁结集在邻港中的希腊各邦全部舰队,这个舰队一经消灭,就会使雅典人称霸海上,没有敌手。阿雷司提狄斯返回大会,并对他们说,泰米托克里斯的计划是最为有利的,但同时也是最为不义的:人民一听这话就一致否决了那个计划。
一位已故的著名历史家非常赞美古史中的这一段史实,以为是极少遇到的一段独特的记载。他说,这里,他们不是哲学家,哲学家们是容易在他们的学院中确立最精美的准则和最崇高的道德规则,并且断定利益是不应该先于正义的。这里是全体人民对于向他们所提出的提议都感到关心,他们认为那个提议对于公益有重大的关系,可是他们却仅仅由于它违反正义而毫不迟疑地一致予以否决了。在我看来,我看不到雅典人这次举动有什么奇特之点。使哲学家们易于建立这些崇高准则的那些理由,同样也趋向于部分地减少了希腊人那种行为的美德。哲学家们从不在利益与正直之间有所权衡,因为他们的判断是一般的,他们的情感和想象都不关心于对象。在现在的情形下,利益虽然对雅典人是直接的,可是因为它只是在一般的利益概念下被认知的,而并不借着任何特殊的观念被想到的,所以这种利益对于他们想象的影响必然没有那么大,因而也不会成为那么猛烈的诱惑,就像他们先已知道它的一切情况时那样。否则我们难以设想,那样一批正像人们通常那样地是不公正而暴烈的全体人民如何竟会一致坚持正义,而抛弃任何重大的利益。
任何新近享受而记忆犹新的快乐,比起痕迹雕残、几乎消灭的另外一种快乐,在意志上的作用要较为猛烈。这种情形的发生,岂不是因为在第一种情形下,记忆帮助想象,并给予它的概念一种附加的强力和活力么?关于过去快乐的意象如果是强烈和猛烈的,它就把这些性质加于将来的快乐观念上,因为将来的快乐是由类似关系与过去的快乐联系起来的。
一个适合于我们生活方式的快乐比起对我们的生活方式是陌生的快乐来,更能刺激起我们的欲望和爱好。这个现象可以由同一原则加以说明。
最能把任何情感灌注于心灵中的,就是雄辩,雄辩能够以最强烈的和最生动的色彩把对象表象出来。我们自己也可以承认那样一个对象是有价值的,那样一个对象是可憎的;但是在一位演说家刺激起想象并给这些观念增添力量之前,这些观念对于意志或感情也许只有一种微弱的影响。
但是雄辩并非总是必需的。别人的单纯意见,尤其是在情感增添它的势力时,会使一个关于祸福的观念对我们发生影响,那种影响在其他情形下是会完全被忽略掉的。这是发生于同情或传导原则;而同情正如我前面所说,只是一个观念借想象之力向一个印象的转化。
值得注意的是:生动的情感通常伴随着生动的想象。在这一方面,正像在其他方面一样,情感的力量一方面决定于对象的本性或情况,一方面也决定于人的性情。
我已经说过,信念只是与现前印象相关的生动的观念。这种活跃性对于刺激我们的全部情感,不论平静的或猛烈的,都是一个必要的条件;至于想象的单纯虚构,则对于两者并没有任何重大影响。虚构过于微弱,不能把握心灵,或引起任何情绪。
(选自休谟《人性论》,关文运译,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