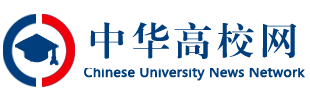阅读王棵的《风筝是会飞的鱼》过程中,有一个真实的故事不断浮现于我的脑海。
2020年6月15日,我国西部边境,陆军某部营长陈红军奉命带队前往一线紧急支援,在加勒万河谷同印军的惨烈搏斗中英勇不屈,为捍卫国家领土主权壮烈牺牲,被追授“卫国戍边英雄”称号。今年7月,中国人民军事博物馆展出的陈红军烈士的工作记事本上,记录着他生前每天常做的一些事情。
和平时期戍边军人的生活,在很多方面其实极为相似,像离家万里之遥,与至爱的亲人聚少离多,工作环境恶劣,手头的事务琐碎单调,等等。在《风筝是会飞的鱼》中,南沙某个礁盘上守礁的海军军官冯加友——因为他爱笑,有一张太阳一样的笑脸,被战友们称为“冯太阳”——几乎是另外一个陈红军。他的任务是戍守中国的南沙岛礁,他所坚守的日常,是极度孤寂、枯燥和乏味的,但他有想法,爱说爱笑,会讲故事,能苦中作乐。有一天,他在突如其来的危机事件中牺牲了——为了救助遇险的渔民,其时,他妻子的腹中已经有了一个小宝宝……对于像王棵这样一位在南沙守过礁的作家来说,很多刻骨铭心的感受,一个特定群体的生活形态和生命价值,可能需要一次更为内在的书写,或者说需要一种特殊的文学转换,才有可能在精神上真正自我“完成”,才有可能彻底释然吧?如此,就有了《风筝是会飞的鱼》这样一本让人心动的、充满了爱的书。
粗略地说,《风筝是会飞的鱼》属于书信体小说,不过,当我们读完这部作品时,就会发现,王棵在小说的叙述方法、时空观念,以及语言风格上的把握是十分恰当的。因为,大到对中国南海概念的表达,小到对南沙礁堡内中国军人生活细节的呈现,都更需要某种现实性或者是精确性的描述。小说中除了交代天候气象,动植物生存条件,也会在写到枪支与子弹使用情况时暗示读者,那里一直维系着和平的,其实是无处不在的“敏感”,备受国际社会关注的南海海域诸岛礁,关乎中国真实的海洋权益,而非鲁滨逊随随便便登上的什么乌托邦荒岛。另一方面,从人的情感的发生发展看,从更加人性的方面考察,小说亦有必要公允落笔。作家写道:“看来,给艾齐写信,不仅仅是因为这位南沙守礁军人觉得艾齐需要有人给他写信,给他讲讲外面的世界,还因为这位军人也需要向人倾诉。”这当然更符合真实的情况,没有比一个数月时间都被“禁锢”于茫茫大海中一块不足篮球场大的礁盘之上的人更需要倾诉了。表面上看,《风筝是会飞的鱼》是一个施爱者、资助者,与一个因父母不幸过早亡故而整天郁郁寡欢的孩子之间的故事,实则是一次关于心灵交往、情感教育,关于人的精神之成长、健全与自足的深情叙述。
少年艾齐以及为他读信的另一个少年夏树,他们与守礁军人冯加友之间的交流是双向互动的。冯加友写信时,一直在想象艾齐的模样,所以,艾齐从每月一封的远方来信中感受到的,显然并非一般资助者的客套话,而是恳切、深情、细腻的絮叨,几乎面面俱到,冯加友已然将艾齐视若己出。而在艾齐这边,冯加友则是“以爸爸的形象住进了艾齐的心里”,缺乏父母关爱的艾齐,对这个南沙守礁军人渐渐有了某种精神依恋。冯加友喜欢做风筝,他寄给艾齐一个用鱼皮做的风筝,艾齐通过这个形状酷似一条飞鱼的风筝,在一次又一次的放飞中,真切地感觉到了“南沙爸爸”的存在。同时,因代为读信而成了旁观者的少年夏树,也被带入到对守卫海疆的军人生活的无限想象之中,并最终在考入大学后入伍,选择去南沙做一位守礁军人……儿时偶然飘落进心田的一粒种子,在合适的土壤、阳光、温度和气候条件下,就会发芽、生根、成长。生命因互相激发、砥砺而获得生机,生活也在不断的探究发现中寻求到意义。我们可以说,《风筝是会飞的鱼》正是在这一点上赢得了自己的读者。
我向来认为,童书写作须格外谨慎,思想上要清澈、透明,讲述时须专注、诚挚。以上述标准来看,王棵的《风筝是会飞的鱼》在方方面面也都做到了。南海的阔大、邈远,守礁军人在风雨和孤寂中的日日夜夜,那里曾经发生的战事、早期的高脚屋以及无时无刻的警惕戒备,在书中都得以详尽呈现。不仅如此,这本儿童小说对同情、理解和爱意的转达,对心灵之间相互倚靠、共同成长的探究,更是严谨到位,令人信服,作品行文中充满了淡淡的诗意,全书有一种朴素的浪漫和恬静之美,有对中国边海防军人生命节操的诚实讲述,而这一切都与作家王棵对细节的倚重有关。
在《风筝是会飞的鱼》的开篇,我们就看到对南海的与众不同的描述:“没有一丝风的晴日里,舒展平滑的海面像一块基底深蓝色、表面敷着薄薄一层炼乳的大玻璃……晴日里的阳光再繁密、再有力,却也只能在抵达海面时瘫软为一层炼乳状的虚光。”这样的细节描写,很显然建立在深切体验与长时间观察的基础之上,没有与大海朝夕相处,就不可能获得。如此精微、细致、生动和一丝不苟的描写,在书中可以说俯拾皆是。在冯加友写给艾齐的信中,南沙守礁的军人们,除了要面对高温、高湿、高盐,以及台风和暴雨这样的严酷自然环境,还要面对极度的孤独和寂寞。海防战士们的“寂寞”“苦累”和“牺牲精神”,该如何向一个孩子讲述呢?王棵同样是求助于诚实与客观,不事任何煽情或夸张。冯加友在信中告诉艾齐,当南沙的阳光照射在人身上时,“裸露的皮肤所能感觉到的是千万根细小的针向他扎来”,而南沙的风,“会让我想到一堵流动的墙,这墙无所不在地堵在我们周围,让我们感觉压抑”。这些感受,非实地体验肯定是无法获得的,而这得益于王棵曾经的守礁生活经历。我想,恐怕只有当作家沉浸于某种特殊经验,然后又以孩子们听得懂并且能够理解的方式“倾诉”时,南海、南沙、礁堡,以及守礁军人的生活世界,才会呈现为真确可靠的鲜活内容,而非刻意营构、先入为主的崇高象征之类。
让一个人的自我充分地打开,有能力去拥抱和接纳,同时也获得感动、相互的怜悯和亲情一般的关联,这是爱的方法而非“叙述”的魔力。在这个意义上,《风筝是会飞的鱼》超越了一般意义上的英雄叙事,书中人物,从冯加友、夏树、艾齐到孔飞,再到秦少校和蒲老师,都是如本文开篇所提到的陈红军及其妻儿那样的寻常人物。我们在阅读这本书时获得的,是了解南沙普通守礁军人生活常态和具体样貌的“教科书”,而在另外的意义上,王棵其实是向我们提供了关于儿童心灵建构、精神成长及生命理想塑造的一部清新图谱。他的探索无疑是成功的。
(作者殷实 系《解放军文艺》副编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