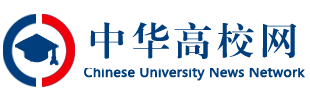编者按
你有多久没有翻过词典了?遇到需要查阅的字词,你是不是觉得点开搜索引擎比翻开词典更方便?但显而易见的事实是,搜索引擎不能代替辞书的功能,因为优质辞书是阅读写作的必备工具,却又不仅仅作为“工具”而存在。优质辞书是人类优秀文化的精华和集成,是一代代语言学家和辞书专家对优秀文化中最精粹、最基础、最硬核知识的总结,体现了学术发展和文化传承。为使读者更深刻地认识辞书,了解辞书,“读书周刊”从本期起推出“辞书有文化”系列,带领读者走进辞书的世界。
辞书是各类字典、词典、辞典和百科全书的统称,也叫参考工具书。谈到词典,人们就会联想到知识和学习,将词典比作“无声的老师”“良师益友”“没有围墙的大学”“知识的宝库”“知识的海洋”等。这些大家耳熟能详的表述也反映了人们对辞书功能的基本认知。辞书具有知识贮藏和解疑释惑的功能,在人类社会发展和文明演进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从“检索”到“悦读”
据相关研究,人类辞书编纂的历史可追溯至4000多年前。人们编纂辞书贮藏和传承知识,使用辞书学习和传播知识,辞书的文化与教育功能不言而喻。“国无辞书,无文化之可言也”(陆尔奎)。辞书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文化产物,不同历史时期的辞书生活往往呈现出不同的时代风貌。在人类辞书发展的前计算机时代,“手与纸”及“火与铅”是传统辞书编纂的典型意象,而纸质印刷的出版形态与辞书文本的篇幅限制对辞书内容选取与编排提出了很高的要求。相应地,人们对传统辞书生活的经验认知往往固化于知识信息的查找与考证。进入计算机时代后,尤其是互联网时代的到来,人类的辞书生活又从“光与电”进入了“网与天”的发展阶段。如今,全媒体或融媒体辞书的时代已成为现实。
随着辞书编纂出版媒介的不断变化,传统辞书的知识贮藏空间与检索效率这两大核心问题得以解决。得益于互联网移动终端的广泛应用,人们的“辞书生活”变得更加便捷高效,可以随时随地查检不同类型的电子或在线辞书,获取相关知识信息,及时满足解疑释惑的多种知识需求。与此同时,互联网空间海量数据迅速累积,人们借助各类搜索引擎获取信息成为求知的新路径,很大程度上拓展了传统“辞书生活”的边界。尤其是“后维基时代”,在“网络知识民主”的浪潮中,传统辞书的权威身份被解构,知识查检与规范功能逐渐式微,似乎已被边缘化。但是,学界也出现了另一种声音,认为“‘我们正淹没在信息中’,但却迫切渴求知识。或许我们是‘信息巨人’,但可能变成‘知识侏儒’”。信息时代人们知识实践中出现的这些新焦虑很发人深思。知识社会,人们的求知方式将如何转变?人们的“辞书生活”方式又如何与时俱进?
纵观人类社会发展史,人们求知的需求与方式有着典型的时代特征,大众“辞书生活”方式也存在显著差异。在以权力为主体的农业社会,因文字识读教育程度所限,普通大众往往偏离甚至脱离“辞书生活”,这个时期各类辞书的编用研习多聚集于少数知识精英群体。到了以财富为主体的工业社会,大众受教育程度得以逐步提高,但知识分化、积累和发展的程度也更高,人们的“辞书生活”多为知识实践问题所驱动,“查得率”与“便捷性”成为辞书查考功能优劣和“实用性”的评判标准。这两个社会历史阶段中,人们使用辞书的主要目的在于查考求证、释疑解惑。进入以知识为主体的知识社会后,知识将逐步成为最关键的生产要素,人们要通过知识的“消费”走向知识的“再生产”,而如何获取并学习更加系统、专业和权威的知识内容是新时代大众知识实践的重要目标。在现代数字媒介助力之下,辞书的传统优势,即提供权威、系统而专业的知识,将焕发出全新的活力。对此,辞书学界和业界已经形成了广泛共识,融媒辞书研发与辞书阅读功能拓展将为“辞书生活”新需求创造更好的条件。在知识社会,辞书不仅要“可查”而且更应“可读”,人们将从以往单纯关注知识查考的“辞书检索”转向重视知识学习的“辞书阅读”,“辞书生活”的新风尚呼之欲出。
事实上,在人们传统的“辞书生活”中,尽管知识信息查考是辞书生活的常态,但中外也不乏通读辞书的使用者。比如,英国“维多利亚时期的诗人罗伯特·布朗宁就曾整本通读过塞缪尔·约翰逊1755年版的《英语词典》,以此作为其自我锤炼诗歌艺术的一种方式。再比如,美国作家阿蒙·谢伊坚持读完了20000多页篇幅的《牛津英语词典》”。在中国,也有学人通读《新华字典》《说文解字》《汉语成语小词典》,甚至是《中国大百科全书》等辞书。这种通读方式虽对读者的恒心与毅力挑战巨大,不具有普遍适用性,但却能够说明辞书知识的系统性具有“可读”与“可学”的潜质。随着现代辞书编纂出版的融媒发展趋势,辞书的数字化编纂与多模态应用为借助辞书学习创造了更为现实的条件。简言之,阅读辞书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苦读”,“悦读”将成为辞书使用的全新体验。
从“深读”到“选读”“翻读”
那么,究竟如何去“悦读”辞书?首先,我们要积极倡导问题驱动,鼓励大家开展知识查考基础上的深入研读,体验“深读有益”的愉悦。这种“深读”,是指词典使用者基于具体查考求知需求而展开的相关研究学习过程。不同于以往将词典仅作为知识查考资源,使用者可充分利用现代辞书的知识学习功能优势,进行基于实践问题的知识研习与拓展,从知其然到知其所以然,深度掌握相关知识内容。这一过程既解决了具体的求知问题,又深化了相关知识学习,往往可以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充分体现了辞书辅助自主知识学习的重要价值。这方面,现代辞书家族中的“学习型辞书”的可学性优势非常明显,对于学习者的帮助更为直接高效。以外语学习为例,在产出型活动中,如写作或翻译实践中,同义词的选择通常是个难点,因而可以基于目标词汇,就其同义词、近义词甚至是反义词,进行问题驱动的深度阅读,反复研究相关条目中的释义、例证和辨析的内容,再结合具体语言产出实践活动进行应用。学习者针对词典中所读到的典型例证进行强化学习,从模仿到创造,相关问题便可以得到较好的解决。
其次,我们应积极倡导自主探索学习,有目标有计划地开展系统知识学习所需的选择性阅读,体验“选读有得”的愉悦。相比于上文所提到的传统意义上通读词典的个例,这种选择性的系统辞书阅读更具现实的可行性。具体而言,辞书用户可根据自己的知识学习目标,选择特定的辞书,再聚焦需要系统性学习的知识内容,自主选择,持续阅读,逐步积累知识。以语文辞书使用为例,词汇知识学习的层次性和关联性是两大关键选择要素。层次性阅读,涉及从单个条目、多个条目到类型化条目的多层次词汇知识学习。单个条目就是最小层级的独立词汇知识系统,完整阅读有助于对词汇知识的全面掌握,符合词汇整体和深度学习的要求。多个条目的选择性阅读,则体现着词汇系统认知的内在要求,学习者通过横组合(搭配关系)与纵聚合(替换关系)两大语义逻辑线索,将多个条目进行关联阅读,必然有利于词汇知识的系统和全面把握。类型化条目的选择性阅读,对于更好地掌握某一类词汇的知识更为有效。比如,高级英语学习者可专门针对英语词汇中高频核心词开展系统学习,选择牛津高阶学习词典中的3000词条目有计划地系统阅读,分批分次进行词汇知识学习,最终词汇产出能力必然会大幅度提升。此外,大量不同类型的专科辞书和百科辞书也都是很好的阅读资源。辞书用户可以根据自身知识学习的个性需求,充分利用当今多模态辞书介质、融媒体传播途径,通过碎片化方式,将所选择内容进行有计划的持续阅读,日积月累,就会逐步完善自己的目标知识储备。
再其次,我们应积极倡导终身学习,开展全民教育意义上的普及性阅读,体验“翻读有乐”的愉悦。正如鲁迅先生1934年所写的一篇短文《随便翻翻》,其中谈到消闲读书的方法,即通过博览群书,积累知识,实现自我教育的一种方式。这方面,辞书的知识内容丰富而且专业权威,完全可纳入人们随便翻翻的范围。当今信息时代,人们利用手机和电脑等电子设备进行碎片式阅读已经成为常态。但网络空间信息庞杂,有些也缺乏依据,从积累知识的角度看,以融媒体形式发布的辞书相关条目内容恰好提供了随便翻翻的优质“悦读”素材。比如,已有不少辞书出版机构通过微信公众号推送多样化的专题性知识内容,实际上就为辞书使用者提供了“悦读”便利。近年来,人们对电子化碎片式阅读的诟病,其实质主要是对阅读内容选择的隐忧。如果大家利用零碎的时间,随便“翻读”来自优质辞书的丰富内容,积沙成塔,应该既能增长知识,又能享受阅读之趣。
转变辞书使用传统观念
托夫勒曾将人类社会划分为四个阶段,即史前时期、农业社会、工业社会和后工业社会。他认为,每一个阶段的演进都是一次新的文明浪潮,而目前人类正在经历第三次浪潮,在实现“知识革命”,也即将进入“信息社会”的全新文明形态。德鲁克在《知识社会》一书中也指出:“我们早已进入一个与以往社会大为不同的社会。……这个新社会就是知识社会,我们现已身处其中。”尽管人类知识社会形态的最终形成或者出现尚存许多有待探究的问题,但当今全球化背景下国际知识经济的发展趋势已经非常突显,“知识社会真正支配性的资源、决定性的生产要素,既不是资本、土地,也不是劳动力,而是知识……价值由‘生产力’与‘创新’来创造,二者都将知识运用于工作之中”。因此,优质与深度的阅读将成为知识社会公民的生活新需求。这一时代发展特点无疑对人们的“辞书生活”方式也将产生深远影响。
在知识社会,对于任何一个国家而言,全民教育与终身学习的理念都是国家富强、民族兴旺和文化繁荣的重要前提与基础。对于个人而言,我们应进一步转变传统辞书使用的既有观念,充分利用现代辞书强大的知识服务功能,开展基于辞书的自主知识学习,倡导“悦读”辞书的全新生活风尚。唯有如此,我们才更有希望去构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知识型社会和创新型国家。
(作者 魏向清系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中国辞书学会副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