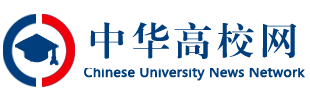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显示,近年来我国总和生育率已跌至1.3,进入了超低生育率阶段;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为18.70%,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占13.50%,将很快进入中度老龄化社会。人口老龄化对我国社会经济发展产生深远影响,破解人口老龄化难题需要多措并举、综合施策,特别是要加强教育政策和生育政策协同,这样才能稳步提升生育率水平,促进全社会人力资本积累,保持宏观经济稳定健康发展。
人口老龄化威胁经济可持续发展
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必然出现人口老龄化。按照联合国1956年确立的标准,一国或地区65岁以上老人超过总人口的7%即进入老龄化社会,1982年又将标准调整为60岁以上老人占总人口的10%。无论是按新标准还是老标准,我国在2000年前后就已经进入了老龄化社会。老龄化的直接原因是低生育率和人均寿命延长,但归根到底是经济发展的结果。从国际经验看,当一国或地区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超过3000—5000美元以后,就会陆续进入老龄化社会。近40年来,我国是全球经济增长最迅速的国家,也是老龄化速度较快的国家之一。除经济增长因素外,上世纪70年代我国开始实行的计划生育政策也深刻影响了国民生育行为,加速了我国老龄化进程。
我国人口老龄化有着自身独有的特点。一是老龄化速度快。1990—2020年,我国老龄人口年均增速较世界平均水平高出0.8个百分点。二是老龄群体规模较大。2020年,我国老龄人口比重较世界平均水平高出2.2个百分点。三是“未富先老”。在全球72个人口老龄化国家中,人均国内生产总值10000美元的占36%,3000—10000美元的占28%,而我国在2002年步入老龄化社会门槛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仅有980美元。
人口老龄化从供给和需求两端威胁经济可持续发展。人口老龄化既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反过来又对一国宏观经济产生深远影响。从供给侧看,2012年我国劳动适龄人口数量达到最高峰,之后出现了劳动力短缺和工资快速上涨,劳动力成本的比较优势不断削弱,劳动密集型产业大量外移,国内生产总值增速逐步下滑。从需求侧看,我国人口总量即将在2025—2030年间达到峰值,之后将逐步缓慢下降,人口负增长在不远的将来即将成为现实。终端消费需求不足将成为制约我国经济增长的长期性因素。此外,人口老龄化还会带来储蓄率下降、社会养老负担加重、人力资本改善放缓、居民收入分化等一系列问题,从不同渠道影响国民经济增长的潜力。
警惕“低生育率陷阱”
我国近年来的生育政策调整并未取得预期成效。为缓解人口自然增长率一再走低带来的问题,我国政府开始积极调整生育政策,先试行推出“单独二孩”政策,2016年起全面放开“二孩”,今年5月中央政治局会议又决定实行“三孩”政策。政府试图通过放松生育限制、提高生育率来改善人口结构和促进经济增长,但这些政策调整并未取得立竿见影的效果。2015—2020年我国新出生人口分别为1655万、1786万、1723万、1523万、1465万、1200万人,折合总和生育率分别为1.5、1.72、1.7、1.5、1.52、1.3。由此可看出,“全面二孩”政策出台后的前两年,生育率明显回升,这主要得益于多年积累的二孩生育意愿在“75后”身上集中释放。之后生育率又快速下行,很快回到政策调整前的水平。
养育成本高是影响家庭生育意愿的主因。社会普遍认为,中国家庭生育率低下的重要原因不是育龄夫妇生育意愿不高,而是激烈的社会竞争使家庭生育行为面临很高的机会成本。除直接生育成本外,养育成本更是居高不下,住房、医疗、教育等负担成为抑制生育动机的“大山”。在微观家庭决策中,父母需要权衡子女数量和质量,子女数量增加会导致生育养育费用增加,从而挤占家庭其他消费支出,降低短期家庭效用水平;同时对多数家庭来说,教育总支出增加往往意味着人均教育支出水平下降,会影响子代人力资本的质量。当理性预期到增加生育给自身消费和子女教育质量带来双重压力时,就构成了对家庭生育行为的有力约束。此外,随着城乡社会保障制度的普及以及养老产业和市场化社会服务体系的发展,养儿防老的社会经济功能逐步弱化。这些因素综合在一起,导致中国家庭的真实生育意愿要显著低于主观生育意愿。
警惕低生育率现象长期化导致“低生育率陷阱”。从国际经验看,当一国生育率降到1.5以下后,低生育率现象就可能形成自我强化机制,掉入“低生育率陷阱”。我国学者对1997年以来总和生育率降到2.1以下的66个国家(地区)进行比较研究发现,有近三分之一的国家(地区)生育率一旦落入1.5以下区间,持续时间均超过了20年。因此,人口变量有很强的惯性,想要摆脱低生育率状态十分困难。我国自1992年起总和生育率低于2.1,2005年后连续15年低于1.5。如果没有其他配套激励措施,单纯依靠放开“三孩”政策,仍难实质性提高国民生育水平。
加强教育政策和生育政策协同
加快完善多元化生育激励保障配套政策体系。人作为生育行为主体,其生育决策受到复杂动机的约束,扭转人们的低生育倾向需要多措并举。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国家多年来鼓励生育的做法经验,生育政策体系主要包括休假制度、女性就业支持、托幼服务、经济补贴等四个方面。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妇女产假时间较短,但研究表明,妇女休假长度和生育率相关性较弱,产假过长还可能使女性面临更高的就业门槛,并影响其职业升迁的机会。另外,我国女性劳动参与率较高,生育孩子的机会成本更高,因此需要重点关注对生育女性就业权益的各种隐性损害。当前,我国城乡儿童入托难、入托贵的问题仍是焦点,亟须加大财政支持和政策保障力度。在经济补贴方面,2018年新个税改革时将3岁及以上子女的教育费用纳入了税前抵扣范围,金额为1000元/孩/月,但面对高昂的生育养育费用负担,这方面还有很大的政策空间。
大力推动教育减负。研究显示,我国现处于成本约束的低生育率阶段,升学竞争压力和教育成本负担是制约家庭生育意愿的因素之一,而课外辅导培训是家庭教育支出的主要负担。虽然我国已普遍实行九年义务教育,但考试选拔的升学压力迫使家长大量选择课外辅导培训。近年来教育产业和市场化机构快速发展,一方面丰富了教育产品供给,成为学校教育的重要补充;另一方面使家庭在学校教育之外对“影子教育”的投入不断增加,形成沉重的负担,同时进一步强化了应试教育导向,扩大了教育不公平。近期,教育行政部门和市场监管部门对校外培训机构进行集中摸底整治,发现普遍存在着不同程度的虚假宣传、盲目扩张、霸王条款等不当竞争行为。因此,应进一步加强对教育培训行业的监管,保障教育商品质量,限制教育商品价格,切实推动教育减负。
加大政府教育投入、推动公共教育服务均等化。20世纪中叶,经济学家舒尔茨提出,人力资本投资是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它既包括人口数量和规模,也包括人口素质和结构。在我国,教育作为人力资本积累和代际转移的重要途径,同时影响着人力资本的数量和质量。要提高生育率和缓解人口老龄化,必须切实降低家庭教育负担,而要提高人力资本积累水平,又必须加大教育投入和资本密度。解决上述矛盾的关键是调整教育支出的结构,由政府代替家庭成为教育成本的主体承担者。为此,应进一步提高国家财政支出中公共教育支出占比,试点探索政府购买服务和发放教育商品补贴;逐步扩大义务教育覆盖年限和范围,提高中考、高考的录取通过率;积极推动教育供给侧改革,将更多音体美劳和通识教育内容纳入基础教育体系。要通过公共教育服务均等化等手段,提升人力资本积累数量和质量,促进我国经济可持续高质量发展。
(作者陈稹 杨书越分别系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