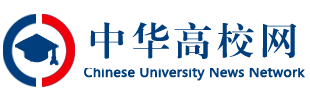40年前,两条麻花辫,一身无畏感。40年后,我仍如此,只是辫已泛白,身已疲病。40余年,有愧,有痛,无悔。40余年,一生只为一事来,1000多名孩子在我执教的山村小学启智。40余年,我是教育扶贫工作的亲历者、见证者。40余年,我失去了右眼视力,右耳听力,但依然还能工作。40余年,回看当年的逆行,我承认特傻,但我依然相信山里人需要我这样的“傻子”。
是什么让我从青春年少坚守到耳顺之年?
最初的梦想
40年前,一个19岁南昌进贤的姑娘执意要去一个教师奇缺、远离故乡的穷乡僻壤任教,她就是“傻傻”的我。
记得第一天费尽周折来到两县交界处的泥洋山深处,来到了这个教学点,看到教室昏暗潮湿,除了旧黑板和拼凑的课桌椅,什么也没有,宿舍窗户都不全,校园也没有围墙,如此现状,我真想转身就走,但天已将晚,很难再离开。那个晚上,村里放电影,大家都去看电影了,学校里没有第二个人,我自己打扫房间,口渴得很,忽然天上来了一阵大雨,我接着屋檐上的水喝了个够。那天夜里窗外山风呼啸,不时传来从未听过的鸟兽的怪叫声,感觉声音就在房间中,恐惧、孤独,我躺在简易的木床上辗转反侧,不停地问自己,选择这样一个离父母几百公里、位置偏远、条件恶劣的山村小学教书到底为了什么?
第二天,门口一堆孩子瞧见我这位新来的老师,一双双纯朴明亮的眼睛里,尽是新奇、期盼和渴望,我心底最柔软的地方被深深触动。心想,城里的孩子、山下的孩子可以享受好的教育,山里的孩子也得有老师啊!我还是先留下来吧——没想到,一留就是40年。
山里的工作和生活条件比我想象的艰苦很多,尤其是晚上,关在房间里睡觉时还要在床边放根木棍,老鼠来啦,敲几下把它赶跑,有一次敲过之后还听到有声音,我打开灯一看,发现床边的椅子上竟然有一条大蛇在蠕动……而千脚虫更是床上的“常客”,一不小心就会摸到。
当地村民对刚到任的我能否留下来,没抱任何希望:她一个外乡姑娘能在这里待得住吗?看到他们的眼神,我的第一念头是不想让他们失望。
我学着开荒种菜解决买菜难问题;学校破败不堪,我就买来材料,把教室修好,把冬日刺骨的寒风拒之窗外,让学生在教室里暖洋洋的;学校设施简陋,我就带领老师们就地取材,搭乒乓球台,挖沙坑……上级也充分肯定了我,1984年我23岁时就被组织上提拔为泥洋完小校长。一年又一年过去了,乡亲们由怀疑的眼神也变成了信任。
在偏远的山村执教,交通是一个问题。我虽身在山上,却不想让自己的见识和思想囿于山中,但在山上只要出门就全靠两条腿,学生的课本、教学用具、生活用品都得肩挑手提弄上山,一趟下来,腰酸腿痛,筋疲力尽。记得有一次,我担着自己的女儿和一些课本、书籍上山,好不容易爬过一个山头歇脚,力气已经用到极限,而天就快黑了,我好焦急,这时好动的女儿却又往山下一道风地跑了老远,我绝望地哭喊着:“你让我哪来的力气带你,(我们)必须天黑前走回去啊……”
再后来我学会了骑摩托车,借了600元钱和朋友合伙买了一台摩托车,600元是当年我一年的收入,我要利用休息时间去干装卸车的活儿,还上这笔借款。但我觉得值,摩托车比肩挑手提提高了不少效率,也让我没有再错过有用的培训和会议,是我在山村与外界联络的信使,还成了那个艰苦、恐惧、孤独、信息不畅年代我为数不多的忠实战友。40多年,从县城到澡下镇的近20公里、再从澡下去泥洋的约40公里,崇山峻岭间盘旋颠簸的黄泥、砂石路,先后报废了我6辆摩托车(今天这条路已经修成了水泥路,从澡下镇至泥洋山肩上的白洋教学点,驱车依然还需要一个半小时)。不记得多少次独自一人起早贪黑走在偏僻无人的山路上,被突然出现的野兽吓趴在地上直喊“妈”;不记得多少次夜里骑车,被灯光吸引的漫天飞虫直钻眼睛、鼻子、嘴巴甚至直接吞进了肚子;不记得多少次摩托车坏在路上,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只能哭着推车爬山。那时候说不怕是假的,只不过我把它视作人生选择的代价和对我的考验,这条路是我自己选的,既然钟情于讲台,就必须面对。再后来,习惯了一些,也找到了克服恐惧的“方法”:只要是我独自步行或骑车时就用唱歌来缓解恐惧,我的歌声比摩托车轰鸣声还大。
克服了执教初期的一些困难,也给了我不少信心,我发誓要成为孩子的光,照亮他们出山的路。我知道在黑暗中光的可贵:夜间在崎岖的山路上来回,只要有手电筒或一束车的灯光,我就不再害怕;在简陋的宿舍里,我自制煤油灯、买来马灯,昏黄的灯光也让我感到踏实、有希望,灯光再昏暗,我也能看很多书。我还要借着这些光,把知识的光亮埋进孩子的心里,点亮他们启智之路。
去与留
“你要是去了那山里头做老师,我一辈子不认你这个女儿!你会后悔的……”19岁那年,妈妈想用这样的话留下我,我却是那样的坚定,软磨硬泡地让她同意我上山;直至临终前妈妈还在劝我:“下山吧,你已在山里教了这么多年了,你们六姊妹算你读书最多,如今你最苦啊!下山吧!妈求你了!”那一刻我的心真的好痛……
回想这40多年,妈妈经常把自己从牙缝里省下的钱悄悄塞给我,捧着母亲给的钱,我热泪盈眶:“娘啊!您给我的钱我收了,有些垫给贫困孩子用了,等女儿有钱了、退休了,一定好好孝敬您!”但她走时我却食言了。
“就你觉悟高,我配不上你!人家都削尖脑袋往山下走,而你还越往更艰苦的地方钻……”曾经,看到夜雨打湿床铺、无处落脚的房间,怜惜我的丈夫这样无奈地向我咆哮着。
“我觉得我不是你的孩子,那些山里娃娃才是你的孩子!”曾经,被冷落的女儿也这样对我诉说。
家人不是不懂我,是太懂我、太爱我!但他们又无法阻挡我。我已经把自己交给了那座大山,交给了山村教育,对山里的孩子,我真的离不开也舍不得。忠孝不能两全,人生就是一边选择、一边放弃,一边拥有、一边失去。这一边,我对家人亏欠得太多,我知道自己不是好妻子、不是好女儿、不是好妈妈,这是我永远的痛。
一年又一年,从“支姐姐”到“支妈妈”,再到“支奶奶”,无数次有人问我:支老师,你会走吗?我回答:我走了,孩子们怎么办?没有知识,他们一辈子都只能在山里受穷。世上有些事总要有人去做,为什么带他们走出贫穷的不能有我?
面对困苦与奉献,当很多人诘问“为什么是我”时,我却问自己“为什么不能是我”。
20多年前我已是残疾人了,首先是甲状腺功能减退,然后是视网膜黄斑部出血,导致右眼失明;1995年的一个晚上,我的右耳钻进一只硬壳虫,以为虫子弄出就没事了,因舍不得耽误课程下山就医,错过了最佳治疗时间导致右耳失聪,声带结节,不能喝凉水;双腿静脉曲张,动了14刀……在这种情况下,还是有人经常问我:“年龄这么大了,做了该做的,付出了那么多,为什么还不下山?”我的回答是:因为山里需要,因为爱,因为我愿意!因为我走的是属于自己的人生路,自己选的,没人逼我,所以跪着我也要走完……尽管有些不懂我的人把我的故事讲出了很多版本,我也不想解释,只想默默走完自己的路,我深知自己教的不光是台下坐着的一些孩子,而是山里父母几代人的希望……
2000年,所有教师都离开了,一所小学、两个教学点的教学和管理工作全部压在我一人身上。我也还是坚定地在“连峰路朝天”的泥洋山上的几个教学点间飞驰奔走。
2007年,担心我身体的丈夫偷偷把我调下山。我走了,孩子们怎么办?我不忍心就这样下山,组织上没找到合适的老师上山,我在山下只待了一天,流了一天的泪,就要求重返学校。
2012年,泥洋教学点撤销,年龄偏大、身体欠佳的我被安排到条件较好的中心小学去任教。家人以为我这下可以下山了,谁知一个比泥洋小学更远更艰苦的白洋教学点需要老师,得知消息的白洋村村民联名请我去白洋教学点任教。我不想让白洋的群众失望,更希望白洋的孩子能够就近读书,怀着对家人的愧疚,我再一次放弃下山的机会,顽强地扛着行李带着泥洋剩下的几个孩子奔赴了白洋教学点,陪着几十名留守孩子,又当全科老师又当妈,为路远的孩子做中饭,为不少孩子买衣服、学习用品……
转眼到了2016年,我可以退休了,却因为山里调不上老师,我还是选择了不退,依然还没有能够下山……尽管年纪一年大过一年,我依然没有想过退休、想过下山。“只要孩子们需要,我就会一直坚守在这里。”
一生只为一事来
“女孩子,总归要嫁人,读什么书”“家里穷,读不起了,读不读都一样”“孩子读不读书是我家里的事,你管不着”!这是家访时我常常能听到的说法。
知识应该能够改变命运,然而过去的山里人却不是人人都这样想。我不愿意一个孩子离开我的教室。
“谁家还没个难事,这是我刚拿的工资,你拿去用,孩子绝不能不读书。”我掏出自己的工资……“女孩子读书有出息了,才是你的福气啊!”一次次走门串户,我是一定要把辍学女孩拉回学校的……
40多年中,很多时候我的家庭都是入不敷出的,为了补贴家用,也为了资助更多的学生,我就在双休日、节假日跟着壮劳力去给大卡车装毛竹、装木头。有次装车出车祸了,我跟着大货车翻了几个滚,昏迷了很长时间才慢慢苏醒过来,到现在右边太阳穴旁还有凹陷的痕迹,每年都会疼几次,但我从未向别人包括家人说起疼的事——不想对外人说,是不想听到有人说我:谁叫你待山里了?不想对家人说,是因为怕家人担心。我希望呈现在别人面前的都是阳光的支月英,直到今天我放下了这些包袱,才愿意把这些往事讲出来。鬼门关躺过的我问自己,为什么我大难没死?可能是考虑到我在山里的使命还没完成吧,所以大难没死的我,非常珍惜活着的每一刻时光,珍惜我的使命,我不仅资助自己的学生,有机会还会资助校外的贫困孩子。
“别人当老师赚钱,你当个老师倒贴钱!你吃这么多苦,是为了什么?”面对朋友这样的疑问,我笑而不语,懂我的人不用解释,不懂的人解释了也理解不了。
我所做的一切都有我看重的价值:
首先是快乐和温暖,让我割舍不下。
“支老师,下个学期我就去别的学校上学了,我能不能亲你一下?”一个即将离开学校的孩子悄悄对我说。
“支老师,你喜欢吃笋吗?明天我挖给你吃啊。”一位手脚勤快的孩子总对我说。
“支老师,我们陪你一起送家远的同学回家吧?要不然你送完他们,就只有一个人回来呢!”一些孩子主动当起“护花使者”。
“支老师,中午到我家来吃艾饼”“支老师,晚上去我家吃散灯面”!再有,村里谁家有喜事,只要碰到休息日,都一定会请我去当“嘉宾”……
无论是泥洋,还是白洋的父老乡亲,都把我当亲人,在我心里他们就是我的亲人,令我感动。比如有一次我发烧不退,一名学生的奶奶给我端来一碗面条,面条上还卧着荷包蛋,她说着理解我的话:“一个人教几十个调皮孩子,你这是累的。”有一次我感冒了很长时间,一个人在山上扛了很久,坚持上完一节课后趴在了讲台桌上,所有的孩子都脱下了自己的外衣或马甲披在我背上,顿时背上像压了一座山……像这样的故事我三天三夜也说不完,我还有什么理由不把学校当成自己的家,不把山里孩子当成自己的孩子呢?
我不能离开,就因为他们的信任,因为他们爱我,那里需要我这样的傻子。
其次是成就感,真实的成就感让我欲罢不能。
在我的努力下,40多年来村里的孩子没有一个辍学。在“润物细无声”中,小村庄的脱贫致富一点点从梦想照进现实。
曾经有人问我过去的学生:“对山里孩子来说,老师意味着什么?”学生回答:“就像抓到一根救命稻草一样。”如果真是像孩子说的这样,作为救命稻草的我怎能轻易离开?师者,何止传道、授业、解惑?更是他们人生路上重要的引路人。
我的青春岁月,陪伴一群又一群孩子的童年,自己的成就便是孩子的成就与明天:
那个曾经读不起书、被我资助的学生刘强,到工业园区做起了“小白领”,成为一家人的希望。
那个聪明女孩彭小红,成为村里第一个本科大学生,在广州成就了自己的一番事业。
那个自己和母亲都是我学生的女孩涂莎,和母亲先后都走上了三尺讲台,成为人民教师,托举起更多孩子的梦想……
山里孩子只有读书才能改变命运,如果连我也走了,那么他们谁来教?为什么不能是我?!
如今,我欣喜地看到,不论是泥洋村小学、白洋教学点,还是奉新县澡下镇的其他学校,办学条件得到了极大改善,这里也有了年轻的支教老师,教育均衡正在逐步实现。
40多年来我低头做事也仰望星空,但我从不跟别人比物质条件,没有可比性。我每天活在感恩中,知恩感恩,我也教育孩子们,恩情不分大小,我们都必须永远牢记在心里,当我们长大了,有了能力的时候,就一定要全力相报……几十年见证了普普通通的我也可以实现自己的价值,也可以为中华民族的教育发展添上自己绚烂的一笔。我想,人这一辈子不一定要做好很多事,只要尽力认真做好一件有益的事,活着就有价值。
当白洋教学点漏风漏雨的泥巴房变成新校舍时,我为学校设计了一个校徽:三棵绿树之间,一只白鸽展翅飞起。绿树,是这大山,白鸽,是每一个能自由飞出大山的孩子。校舍的墙壁上,我写了一句话:给孩子温暖,给孩子希望,给孩子力量。
我和无数用责任与爱心投入脱贫攻坚战的人们在一起,不是因为有了希望才选择坚守,而是因为坚守才有了希望。我的肩上有多份更重的责任,一份更重的担当。我谨记自己是一名光荣的党员老师,更是一名倾听民声,反映民意,为群众讲实话,做实事,为民代言的全国人大代表。我将坚守希望,坚守心底永恒的承诺,没有休止符!
(支月英 作者单位系江西省宜春市奉新县澡下镇白洋教学点)
《人民教育》杂志2021年第17期,原题为《一生只为一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