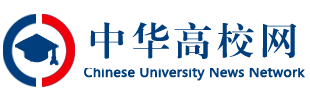周树人何以成为鲁迅
◎主题:周树人为什么会成为鲁迅?
◎时间:2021年9月25日19点
◎嘉宾:陈漱渝 鲁迅研究专家,北京鲁迅博物馆前副馆长
姜异新 学者,北京鲁迅博物馆研究室主任
“所仰仗的全在先前看过的百来篇外国作品”
姜异新:今天(鲁迅生于1881年9月25日,编者注),鲁迅先生140岁了。他在36岁的时候写了中国第一部划时代的现代小说《狂人日记》。在座的朋友们,可能率先进入你们视野的鲁迅就是这样一个小说家。
其实那时候他的本名叫周树人,是北洋政府教育部的佥事。他有一个身份是通俗教育委员会小说股的主任和审核干事。当时全国所有创作的小说、翻译的小说,乃至刊登小说的杂志,都要送到周树人这里来评审——写得好的小说要褒奖,格调低下的要查禁。工作之余,周树人还抄校古籍,做《古小说钩沉》,编《唐宋传奇集》等,写了第一部中国小说史,在北京大学等各个高校讲授这门课。这么看来,在1918年《狂人日记》发表之前,也就是周树人成为鲁迅之前,这个人读过的古今中外的小说实在是多到不可计数。
成为新文学之父后,也就是周树人成为鲁迅之后,经常收到文学青年的来信,讨教作文的秘诀。鲁迅的回答是创作没有秘诀,并说自己从不看小说做法之类的书,只是多读作品。1933年,应邀谈一谈创作经验时,鲁迅写了《我怎么做起小说来》一文,终于道出了类似秘诀的经验谈——“所仰仗的全在先前看过的百来篇外国作品”。
然而,鲁迅的小说阅读太海量了,从留学回国到《狂人日记》发表之前,还有近十年所谓的沉默期,这期间其实他也在大量审读小说。那么,我们如何去界定他说的“百来篇”?这就需要留意一下“先前”和“做学生时”——鲁迅在各种语境下多次提到的时间状语,其实指的就是1902-1909留学日本的这七年。我们知道,在江南水师学堂、江南陆师学堂附设矿路学堂读书时期,是周树人第一次接触西学,课余时间也全部用来读《红楼梦》等中国古代白话小说。但在后来鲁迅述怀的语境中,“先前”“做学生时”都特别指向留学日本这七年。“百来篇”指的就是这期间他用外语去读的外国作品——一开始是通过日语的转译来阅读,后来通过德语直接阅读原版的东欧或者其他国家的小说。
那么,鲁迅留日七年是如何度过的?他是怎么留学的呢?我们知道,鲁迅在江南水师学堂接触了英语,在陆师学堂的矿路学堂接触了日语、德语,但还都很浅显。获得官费留学资格后,初抵东京的最初两年,他是在弘文学院系统学习日语,学科知识相当于日本的中学程度。两年后选择专业,据他说为了救治像他父亲一样被误治的病人,战争时期就去当军医。于是,他来到了位于日本东北部的仙台医学专门学校,学习医学一年半。“幻灯片事件”后,再度回到东京,专心从事文艺运动,其实最主要的就是翻译外国作品。他倾向于俄国、东欧、巴尔干小国被压迫民族的作品,因为感到这才是为人生的、抗争的、刚健的、赤诚的文学。这个时期最长,有三年之久。所以,鲁迅留学时代影响了他精神走向的其实是海量的阅读。这七年间,持续不间断的学习行为就是阅读和翻译。
“从别国窃得火来,煮自己的肉”
姜异新:相比之下,仙台时期少了点,但这个仿佛对文学阅读按下暂停键的一年半,却是不可或缺的桥梁。为什么这么说呢?清国留学生周树人的外语水平在这个时候获得了质的飞跃,无论是日语还是德语,也无论是口语还是书面语。我们都知道,藤野先生给鲁迅批改医学笔记,把他画得特别好看的下臂血管给订正了,但其实通览医学笔记,藤野的大部分修改是关于日语表达和修辞方面的。因为藤野先生那时候也刚刚评上教授,他还是副班主任,周树人是他的第一个留学生,当然也是仙台医专第一个中国留学生,所以,藤野先生非常负责任。那时候也没有多少教材和教辅书,所谓医学笔记就是对老师课堂口述的笔录。所以,老师讲的课一定要非常认真听,然后才能够记下来,也没有参考书去参照订正。所以,藤野先生批得也特别认真。周树人的日语口语、听力和书写便得到了极大提升。再就是他在仙台医专开始正规修德语课,课时也非常多,德语水平也有了很大提升。
今年是鲁迅诞辰140周年,有很多大的文化工程结项,以向民族魂致敬。其中,国家图书馆出版社与文物出版社联合编辑的《鲁迅手稿全集》七编78卷也即将出版,这是历来收入鲁迅手稿最精最全的全集。在这78卷里,我认为最特别的就是医学笔记,典型的用钢笔从左至右横写的现代体式的笔记,里面有汉、日、德、英、拉丁等至少五种语言。而其他手稿可以说全部都是鲁迅用金不换毛笔竖写的传统中国式手稿。当然,小字条不在比较之列。
从医学笔记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索居仙台在鲁迅文学生命进程中的独特性。随着外语水平的提高,之前没太读懂的故事一下子心领神会了,一下子摆脱日语翻译的中介限制,可以直接用德语去读懂原版东欧故事了,对世界文学的渴求愈加强烈,想读得更多、更深、更远。再加上日俄战争的时事幻灯片在细菌学课堂上播放,因为日俄战争开战的战场是在中国的东北,只要是一个中国人,看到这样的幻灯片没有不受刺激的,当然也深深刺激了鲁迅。
所以,内驱力加上外在的导火索,鲁迅很快就辍学再度回到东京,要“从别国窃得火来,煮自己的肉”。我们知道,明治时期的日本是中西文化汇通、世界文学窗口的敞开地之一,信息传递非常迅捷,翻译界更是立足世界前沿,引领社科思潮,很多世界著名文学家像向往巴黎一样地向往到东京沉潜。鲁迅也再次来到东京,开始了自主阅读学习的三年。他已经不去专门的学校了,完全是海量阅读的留学方式。而且他的二弟周作人也来到东京,周作人是非常精通英语的。所以我们寻绎的这“百来篇”包括鲁迅用日语、德语读的小说,也包括英语。实际上,鲁迅在江南水师学堂就读期间是接触过英语的,他也能够借助词典、借助周作人的视野和帮助,去阅读英文版的作品。
为什么留学日本时首先关注俄国文学
姜异新:再度回到东京的三年,鲁迅下的功夫非常大、非常深,常常整夜不睡地阅读翻译外国作品,留在茶几上的是像马蜂窝一样插满了烟蒂的烟灰缸。鲁迅所说的“百来篇”主要就是这一时期苦读的作品。其实,初抵东京时期,周树人就已经开始“盗火煮肉”了,开始翻译外国科幻小说。只不过,他的肉身还没有觉察心灵的渴求,还在顺遂学校的选科制度,为未来的职业做出有限的选择。而经过仙台的转换,一下子接通了文艺心灵的道交感应。
既然鲁迅留学日本的七年以海量阅读为主要学习方式,那么,他提到的“百来篇外国作品”到底有没有一个详细的书目?鲁迅从来没有明确地陈说。这就仿佛构成了一个谜,成为很多关注鲁迅阅读史、文学家鲁迅创生史的学者们穷究破译周树人之所以成为鲁迅的密码。
我主要从五个方面依据入手来寻求、探索和推测。简单说来:第一是剪报;第二是翻译作品,特别是已出版的《域外小说集》,还有打算翻译的出版预告;第三是周氏兄弟回忆文字;第四是文学教科书;第五是藏书视野下的经典周边及潜在阅读。通过探究,我发现至少有140篇外国作品是能够与鲁迅在留日时期通过外语读过的外国作品挂上号的。
第一部分剪报,这是实实在在的物证,是鲁迅从日本带回来的日本人翻译的十篇俄国小说的合订本,包括屠格涅夫、普希金、果戈理、莱蒙托夫等作家的作品。但我不把它仅仅看成是一个剪报,我觉得这是鲁迅以他自己的审美眼光编选辑录的俄国作品集,也是他自己装订成册为一本新书。我们对这十篇作品进行了故事的缩写。
第二就是他翻译的小说,这肯定是他反复咀嚼过的作品。这里我只提一下《域外小说集》里的16篇。我们看到,第一册基本还是俄国文学占主体。为什么鲁迅留学日本时首先关注俄国文学?我认为是日俄战争的巨大影响。这应该是鲁迅最初关注俄罗斯文学的外部因素。在明治日本梦想着文明开化、富国强兵、领土扩张的国民昂扬感中,如何拨云见日、驱散迷雾,初步形成自己的俄罗斯观,这是周树人的独立思考。其实俄国并不是后来他说的东欧弱小国家,而是西方的列强之一,周树人要看看雄起于广袤原野上的西方强国俄罗斯的土地上生长着怎样的人民。一开始他只能通过日语去了解。其实他也学了几天俄语,后来放弃了。当看到原来也有被侮辱被损害的小人物,也有被剥削到连短裤都没有剩下的农民时,他反而获得一种心灵得以深入沟通的艺术愉悦——这片土地上孕育的作家具有如此宏阔的视野,如此超然洞悉人性的笔力,产出了真正为人生的刚健的文学,促使他理解了在中国的土地上旋生旋灭的种种现象。
更多发挥工具书作用,体现领读宗旨
姜异新:其实第二次来到的东京,对周树人来说已经不是地方上的东京,而是世界的缩影,就像20世纪20年代的巴黎一样,吸引众多文艺家聚集在咖啡馆形成一个文学群落,东京也具有吸引不少他国作家去沉潜的文化魅力。鲁迅也是在这里集中阅读了三年。连日本人的杂志都关注到周氏兄弟的阅读行为,特别是他们要摆脱开日本,把外国故事直接用汉语介绍到中国去的翻译活动。所以,《域外小说集》中的作品虽然鲁迅只翻译了其中的三篇,但是全部16篇都经过了他反复的审读、润色和修订。这些故事我们组织学术力量,依据最初的东京神田版对周氏兄弟的文言译本进行了白话重译。
再一个就是文学教科书。再度回到东京这三年,虽然周树人不去到全日制的学校上课,可是他也是把学籍挂在独逸语学校。日本学者考证出了学校的文学教科书以及暑期阅读的文学书目,我也对照馆藏鲁迅藏书书目,筛选出一些间接证明鲁迅那时可能读过的外国作品。
最后,就是通过周氏兄弟的回忆文字和其他线索推断出来的作品,设为“其他”一辑。我们拣选了一些有代表性的作家作品进行了缩写。比如,鲁迅特别喜欢的夏目漱石、显克维支,还有人们不那么熟知的克尔凯郭尔等等。
再次阅读鲁迅留学时代阅读的故事,其实很容易发现他个性化的审美倾向——那些洞悉人性幽暗的作品,举重若轻、让人含泪微笑的表现手法,现代主义的意识流,后现代主义的英雄戏仿,对于被损害被侮辱的小人物的现实主义关怀,等等,显然这是多维复杂的艺术综合体,鲁迅那个时候全部都接受了。编这本书之前,我会觉得鲁迅真的是天才,而且不可复制,能够用中国古代文人乃至近代以来的作家都意想不到的方式,在最简短的篇幅内把故事讲述得如此生动、深刻、直抵心灵;看了鲁迅读过的小说后,我就有一种豁然开朗的感觉,仿佛置身于鲁迅当年置身的精神谱系的网络当中,感同身受,与他一起感动,一起愉悦,审美能力一起成长,同频共振。
遗憾的是,这本书仅仅收了有鲁迅直接阅读证据的38篇小说。其实,我们还缩写了不少外国作品,限于篇幅,暂时没有收入。当今是一个轻阅读的时代,考虑到做一本非常厚的书,大家可能很难读完。不过,在书的最后附了“百来篇”篇目的列表,除了作家作品的名字,还有鲁迅阅读的直接证据和间接证据。所以说,《他山之石》发挥的更多是工具书的作用,体现了领读的宗旨——引领大家循着鲁迅的目光去继续探索、深读原著原版小说。如果大家喜欢,以后可以再出续编,真正呈现给大家鲁迅读过的“百来篇”。
“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新一国之小说”
陈漱渝:今天,大家都承认鲁迅是文学家,而为鲁迅奠定文学家地位的则是他的小说。
而事实上,鲁迅最初是通过翻译活动走向文坛的,最早的成果是跟二弟周作人共同编译了《域外小说集》。这本书得到朋友资助,在日本东京分上下两册出版,在上海市找了一个绸缎庄寄售。上册印了1000本,卖了20本;下册印了500本,也只卖了20本。后来这家绸缎庄着火,存书和纸版也随之灰飞烟灭。这本书被冷落的原因之一,是因为当时的读者还不习惯于短篇小说这种文体,不知为什么文章刚刚开头就很快结了尾。中国人看惯了章回体,动不动要看八十回或一百二十回才过瘾,看戏也要看连台本。
中国读者是通过鲁迅1918年5月在《新青年》杂志发表的《狂人日记》才开始接触现代短篇小说的。在中国古代,“小说”这个名词概念不清,又缺乏科学分类,但实际上存在着文言小说跟白话小说这两个传统。直到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从油印讲义到学术专著,中国古代小说的发展才被梳理出一个粗略的历史轮廓。所以鲁迅1923年10月7日在《中国小说史略》中写道:“中国之小说自来无史……此稿虽专史,亦粗略也。”
1918年4月19日,周作人在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小说研究会发表演讲,题为《日本近三十年小说之发达》。周作人说,在中国传统观念中,写小说是一种下等行为。1902年,梁启超发表了《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一文,提倡“小说界革命”,把小说视为改良社会政治的重要工具。文章开头第一句话,就是“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新一国之小说”。由于新小说可以培养国民新型的道德和人格,激发国民的爱国精神,达到改良政治的目的,所以“为文学之最上乘”。上乘就是上等。
但是,虽然有梁启超大力倡导,“新文学的小说却一本也没有”“算起来却毫无成绩”。因此,周作人希望中国的小说家能借鉴日本小说的创作经验,这经验用五个字来概括,就叫作“创造的模拟”。周作人所说的“模拟”就是我们所说的“借鉴”。“创造的模拟”就是在借鉴的基础上加以创新、实现跨越。中国的新小说不仅要具有新的形式,同时也必须表达新的思想,这就需要从头做起。我认为周作人这种新小说观,鲁迅也是认同的。如果说,胡适和周作人是中国现代小说的理论倡导者,那么鲁迅就是这种理论在创作领域的开拓者和奠基人。
鲁迅创作的小说并不多,结集出版的只有《呐喊》《彷徨》和《故事新编》这三种,一共收录的作品33篇。我以为,仅凭《阿Q正传》这一篇就可以使鲁迅在“文学家”这个称谓之前再加上“伟大的”这个定语。阿Q这个精神典型很快大踏步地进入了世界文学典型人物的画廊,所以鲁迅也就成为了世界级的作家。他不仅属于中国,而且属于人类。
《他山之石》为鲁迅研究提供新的学术增长点
陈漱渝:创作小说,首先要有坚实的生活基础,丰富的人生阅历,深邃的思想穿透力。但同时还必须汲取中外文化滋养,否则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鲁迅在《我怎么做起小说来》这篇文章中明确说过,他创作小说之前并没有读过“小说作法”之类的理论书籍,而“所仰仗的全凭先前看过的百来篇外国作品和一点医学上的知识”。众所周知,鲁迅在日本仙台医学专门学校学过医。他塑造《狂人日记》中那个“迫害狂”的形象,就仰仗了一些神经内科方面的知识。
至于他以前究竟读过哪“百来篇”外国小说,我原先觉得是一个永远解不开的谜。离开了人证、物证、旁证,谁有本领开列出这百来篇外国小说的篇目呢?从1989年起,我开始研究鲁迅藏书,并发表了一些短文。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我又申报了一个集体科研项目,就叫《鲁迅藏书研究》。我的同事、师姐姚锡佩在查找鲁迅收藏的剪报时,发现了一册装订好的日译外国短篇小说,这就是鲁迅留日期间阅读日译外国短篇小说的物证。这一发现增强了我探寻鲁迅1918年之前所接触的百来篇外国小说的浓厚兴趣。从那时到现在,差不多是30年了。所以,我说《他山之石》的出版,是实现了我30年来的一个夙愿。
如果从1909年日本东京出版的《日本及日本人》杂志第508期,报道周氏兄弟的翻译活动算起,鲁迅研究已经有了112年历史。经过一代又一代鲁迅研究学者的共同努力,鲁迅研究已经成为了一门相对成熟的综合性学科,也可简称为“鲁迅学”。这门学科的史料已经基本齐备,今后很难再有能产生轰动效应的发现。对鲁迅评价也基本正确,很难产生颠覆性的看法并能在鲁研界占据主流。
对鲁迅作品阐释当然空间无限广阔,但鲁迅对自己的很多代表作已有自评,研究者对这些作品的理解也很难超越鲁迅本人的自我认知。所以,鲁迅研究学科水平的提升可以说是遇到了一个瓶颈,致使有的学者知难而退。有个别学者则通过过度阐释或故意曲解的方式哗众取宠,吸引大众眼球。
《他山之石》的出版,为鲁迅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学术增长点。读者不应该仅仅关注鲁迅哪篇小说受到了哪位作家的具体影响,比如《狂人日记》的篇名取自果戈理的同名小说,《药》的结尾有安特莱夫似的阴冷……这样的例证是有限的。我们应该通过阅读这本书,进一步研究鲁迅在创作中国现代小说时在文体上进行的大胆探索,比如《狂人日记》《阿Q正传》《一件小事》《头发的故事》为什么形式都很不一样?特别是《故事新编》,为什么又采取了古今穿越的手法?鲁迅对这些外国小说精神上的继承和发扬更值得关注。鲁迅讲得很明白,他在外国文学作品中寻求的是反抗和叫喊的声音。他从俄国文学作品中明白的大事是世界上有两种人——压迫者和被压迫者。所以,我们从鲁迅的阅读和翻译的文化取向中应该学习的首先是鲁迅的平民立场,以及对恶势力的斗争精神。这在任何时代都是为人处世的基本素质。整理/雨驿